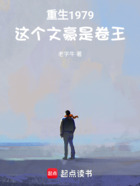
第4章 沙坨子上放羊的
这人物设定、这核心想法都太新奇了,还有这节奏,快而爽但又细节满满,一环套一环欲罢不能。
七八十年代,还没有“脑洞”这种说法,长篇小说的写法也都是娓娓道来。
而苏文天把后世网文的脑洞设定方法,以及快节奏的套路融进了这篇作品中。
这跨世纪的“爽文”手法让上官尧耳目一新。
上官尧就这么站在桌旁,一口气看到最后。
读完最后一个字,还不甘心地翻一下稿纸,遗憾地确定后面真没了。
“不对,这不应该是结尾啊。”
上官尧发现小说没写完,这让他有点心里痒痒,不由得嘀咕出声。
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腿都站麻了。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酸麻的双腿,上官尧闭着眼睛思索:
这么快的节奏,这简短的语句,很有一点海明威的风格,我喜欢。
当然这不可能真的是海明威,时代背景对不上。
不是海明威,这是翻译哪个外国名家的作品呢?
重新翻回开头:稿子里并没有标注翻译自哪部外国作品。
难道是……原创?
一个龙国人写外国作品,味道能这么纯正吗?
不管是翻译还是原创,文笔如此成熟,应该是个老作家。
如果是新人,那绝对是……天才!文坛的未来之星!
上官尧不再思考,拿起纸笔——
【苏文天同志:您好,诚挚地感谢您来稿,有些问题请不吝赐教。】
【您这是翻译作品吗?如果是,请注明原著书名和作者,还有这个作品是不是没写完?您以前发表过其它作品吗?您的笔名是……】
……
千里之外,苏文天站在沙坨子上乜呆呆地盯着老山羊啃草根。
他无法看到上官尧的样子,但不耽误自行脑补。
他想象着上官尧少见多怪的样子,心想如果自己在旁边该多有意思。
他会拍着老同志的肩膀调侃:“上官老大,震惊了没?四十多年后的网文套路如何?”
揣摩着编辑部那几个元老,他在心里笃定:这些老家伙们绝对会被这套路“套牢”。
套路之所以成为套路,那是因为它可以拿捏人心,并经历过无数读者和漫长的时间考验。
“嘿嘿,老上官,你逃不出我的套路。”
一阵山风吹来,苏文天裹了裹老棉袄,踢一脚正在努力寻找草根的头羊:
“走,回家,你吃得差不多了,我还饿着呢。”
头羊“咩咩”地叫两声,不情愿地在苏文天驱赶下往回走。
另外两头羊也恋恋不舍地跟在后面。
这三头羊其实是生产队的。
当年苏文天从监狱里出来后,一改过去憨傻肯干的性情。
他根本不下地干活,就愿意跟知青们“纠缠”在一起,天南地北胡侃、讲故事,还搞什么文学社。
但毕竟还有一个妹妹需要养活,还得柴米油盐,还得挣工分。
在苏文天不断“以德服人”的反复折磨下,生产大队长无奈将放羊的活儿交给他,并按满勤记工分。
放羊、玩文学、跟女知情眉来眼去……
苏文天出狱后的日子就这么慢慢地熬着,他在等待时机,等待着一飞冲天的那一刻。
让苏文天没想到的是,时机还没到爱情却不期而至。
其实,当年苏文天揍王大巴掌的事,究其根源是跟林如心有关系的。
王大巴掌之所以找老李麻烦,起因就是王大巴掌有一次对林如心欲行不轨,被老李撞见。
老李一顿装傻充愣搅了王大巴掌的好事,从此就没了消停日子,隔三差五就被王大巴掌欺负。
然后,被苏文天碰到,苏文天就打折了大巴掌的腿。
有了这一连串的因果,苏文天出狱后,林如心对他也是另眼相看心存感激。
接触之后,林如心惊奇地发现,以往觉得憨憨傻傻的苏文天原来是个“文学宝藏”。
什么诗词歌赋,古典现代,张嘴就来。
对于刚刚出现的那些让人读起来云里雾里的诗歌,苏文天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还专门为3月份刚发表的北岛的诗作《回答》写了一篇诗评。
诗评名字叫《朦胧诗——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幻灭》。
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他们知青点内部讨论的文章,有好事者将该诗评传给其他知青点的诗歌爱好者。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在诗歌爱好者中传播开来。
甚至传入了大学校园、教授案头。
从这篇诗评开始,那些云里雾里的诗歌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朦胧诗。
对于当代的那些小说,苏文天更是了解得让人瞠目结舌。
什么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苏文天张嘴就来。
在全公社“知青文学社”的一次大讨论中,他又写了一篇《我姑且称他们为“伤痕文学”》的评论文章。
文章洋洋洒洒,不仅对“伤痕文学”进行了定义和概述,还对其出现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进行深入剖析,更大胆地预测未来还会出现“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各种各样的流派。
这篇评论文章和那篇诗评一样,也很快流传开来,在各地知青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来传去。
在这个人人都自诩为“文学青年”的年代,众多年轻人没读过《班主任》《伤痕》也看不懂《回答》,但他们都会附庸风雅地谈到“朦胧诗”和“伤痕文学”。
尤其是“朦胧诗”,许多人按照《朦胧诗——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幻灭》这篇诗评里提到的写作方法,创作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朦胧诗”。
“朦胧诗”如春笋般到处冒头,似乎满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写“朦胧诗”。
在这两篇文学评论迅速成为“时尚文学”标签的同时,名字怪异的作者“沙坨子上放羊”也成了神秘的地下“文学评论家”。
很多文学教授、诗人和作家都在寻找这个“沙坨子上放羊”,有人想跟他探讨文学,有人想请他给写评论……
可是,这人太神秘,不在大学校园里、不在工厂矿山中、不在建筑工地、更不在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电台,全国基层群众文化馆里也没人知道这个人。
没有一个作家、编辑和文化工作者了解这个人。
“沙坨子上放羊”成了文学界的一个传说。
文学界在找“沙坨子上放羊”,而苏文天根本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找自己。
那一刻,他正沉浸在沙坨子上的爱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