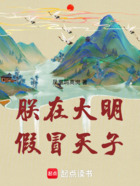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55章 朕才不当“天顺帝”
其实伯颜帖木儿这时是犯了一个典型的经验主义错误,他见朱祁镇对石亨调任的回应是“磨砺人才”,又得知于谦调石亨回京是为拱卫京师,便想当然地认定石亨必是大明不可或缺的大将。
更因阳和口一役瓦剌赢得太过轻松,眼见这个昔日的手下败将在短短数日之内,竟能在大明重获提拔,伯颜帖木儿便断定,大明已经是将才凋零,无人可用,只要朱祁镇能配合叫开大同城门,华北唾手可得。
他根本想不到这背后所暗藏的种种朝堂博弈,更未参透朱祁镇那番话中的弦外之音,皇帝表面夸赞石亨,实则是暗讽于谦借调任将领之机收买人心。
而且伯颜帖木儿虽然有个汉人母亲,熟知经史典故,但他对中原王朝的实际政治运转始终如雾里看花,略知皮毛而已。
他压根无法切实理解“天子”二字背后所承载的天命神性与无上权威。
在他眼中,中原皇帝只是一个更强大的“大汗”,在草原上,废立大汗如同更换马鞍般寻常,而大明在皇帝被俘后竟耗费三日才确立储君,简直迟缓得不可思议。
因此伯颜帖木儿完全无法共情朱祁镇内心的煎熬与矛盾。
在他的认知里,既然已探得于谦正在调兵遣将、整顿京防,这不恰恰说明京师空虚?
此时不趁郕王尚未正式登基、正统天子余威犹存之际,借瓦剌铁骑叩开九边雄关,长驱直入夺回帝位,又更待何时?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般明摆着的上策,朱祁镇为何还要痛苦纠结成这副模样?
直接杀回紫禁城,将郕王、于谦等人尽数诛灭,皇位不就自然物归原主了吗?
若说先前因不了解朝中情形,朱祁镇尚存几分幻想倒也情有可原,可如今郕王僭越之心已昭然若揭,按常理该以牙还牙才是,这小皇帝怎么还在优柔寡断、踌躇不前?
伯颜帖木儿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只能从朱祁镇先前的两次情绪崩溃中寻找突破口。
他敏锐地注意到,这小皇帝在失控时总会流露出想要超越其曾祖父与父亲的执念。
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调整劝说策略,“昔年齐泰、黄子澄蛊惑建文帝削藩,太宗皇帝以‘清君侧’为名挥师南下,终成永乐盛世,如今于谦离间天家骨肉,岂非正是当年的齐、黄之流?”
“只要陛下现在再下一道手谕,以‘肃清朝纲’为名,命刘安、郭登开启大同城门,不消旬日,我军便可兵临北京城下,届时生擒郕王、问罪于谦,陛下既可光复大统,又能效法太宗皇帝伟业,岂不两全?”
帐外北风凄厉,他刻意将“太宗伟业”四个字咬得极重,暗红的火光在他脸上投下诡谲的阴影,将这番说辞渲染得愈发蛊惑人心。
朱祁镇却像患上了突发性耳聋,他收回悬在空中的手臂,整个人重新沉入氤氲着热气的浴桶中,专心致志地泡起澡来。
伯颜帖木儿接着道,“陛下莫非以为,您就此错失良机,郕王便会感恩戴德?”
“昔年靖难前夕,建文帝已先行废黜了青州齐王与大同代王,待燕师起兵,辽东辽王、宣府谷王更是纷纷弃藩归京。”
“彼时太宗皇帝麾下仅有一支燕军,而宁王却坐拥八万精甲、六千革车,更有朵颜三卫铁骑助阵。”
“建文帝为防‘燕宁合流’,急诏宁王返京,当此生死之际,宁王只有两条路,要么即刻起兵助燕,要么奉诏南归,可他却偏偏首鼠两端,滞留大宁,观望徘徊。”
“于是太宗皇帝的佯装穷途末路,自刘家口间道疾驰大宁,假意向宁王求援,宁王不疑有诈,竟单骑出迎太宗皇帝入城,太宗皇帝执其手痛哭流涕,自称起兵实乃迫不得已,更央宁王代拟请罪奏章。”
“如此盘桓数日,宁王始终以诚相待,殊不知燕军精锐早已暗伏城外,将士渐次潜入,更与朵颜三卫暗中勾结。”
“待太宗皇帝辞行,宁王亲至郊外饯别之际,伏兵四起,将其劫持,朵颜三卫闻风响应,守将朱鉴虽力战而亡。”
“顷刻之间,大宁易主,王府家眷尽入松亭关,大宁为之一空!自此太宗皇帝尽收大宁雄师,更得宁王亲拟讨逆檄文,声势大振。”
“按常理,宁王既是被迫从叛,本可得建文帝宽宥,奈何他手握重兵,又得太宗皇帝‘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之诺,自此便与靖难之师绑在了一处。”
“待太宗皇帝收编大宁铁骑后,立即打散旧制,重整部伍,以致建文帝的平叛大军在战场上遇见宁王旧部,照样刀兵相向。”
“此例足以证明,但凡身陷敌营而未以死殉节者,在朝廷眼中便是十恶不赦的叛臣!陛下滞留漠北日久,今日更为我瓦剌请赏,在郕王眼中,只怕早已将您视作亡国之君了!”
“就连那些被明军俘虏,怕也一同成了投敌叛国之徒!陛下即便不念及自身荣辱,也该为那些无辜将士谋一条生路啊!”
伯颜帖木儿一面说着,一面重重地拍在浴桶边缘,激起阵阵水花。
朱祁镇被这番动静搅得心烦意乱,蹙眉回道,“太宗皇帝靖难时不过一藩王,自然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朕本就是九五之尊,何必效此掩耳盗铃之举?你是要朕自己清自己吗?”
伯颜帖木儿回道,“就是自己清自己!陛下,这种事,我们蒙古人再熟悉不过,您可听说过蒙元的‘两都之战’吗?”
“昔年元成宗驾崩,卜鲁罕皇后垂帘,安西王阿难答辅政,因安西王阿难答崇信色目回回教,而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推崇汉制,两兄弟遂联合右丞相哈剌哈孙发动政变,一举囚禁了卜鲁罕皇后与安西王,元武宗登基为帝。”
“元武宗与元仁宗为了维持汉化改革,立下‘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之约,史称‘武仁授受’,结果元仁宗继位后,竟背弃誓约,改行汉家嫡长子制,驱逐元武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元英宗为帝。”
“元英宗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推行汉化,不仅衣冠礼乐尽仿汉制,还在祭祀太庙时公然身着汉家冠冕,躬行汉礼,最终因触及蒙古保守派的利益遇刺身亡,是为‘南坡之变’。”
“元英宗被杀后,元仁宗一脉绝嗣,蒙古保守派为防再出汉化之主,遂拥立元世祖嫡孙晋王即位,是为泰定帝,泰定帝为了防止身后出现皇位之争,登基次年便立四岁幼子阿速吉八为储君。”
“岂料天不假年,泰定帝在位仅五载便因病去世,偏生又驾崩于上都避暑之时!依照蒙元旧制,帝王每年四月北巡上都,八月方返大都,泰定帝这一死,朝政尽落丞相倒剌沙之手。”
“这倒剌沙早在南坡之变时就有拥立之功,泰定朝更是权倾朝野,如今幼主在侧,他却迟迟不肯行册立之礼,朝中汉化派见此良机,再度蠢蠢欲动,意图拥立元武宗之子为帝。”
“元武宗膝下共有两子,长子和世㻋被元仁宗放逐云南,此时已西逃察合台汗国,而次子图帖睦尔被流放至海南琼州,泰定帝即位后出居江陵。”
“汉化派本想拥立长子和世㻋,奈何关山阻隔,远水难救近火,于是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当机立断,联合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星夜兼程将驻守江陵的图帖睦尔迎入大都,仓促间黄袍加身,改元‘天历’,是为元文宗。”
“倒剌沙在上都见势不妙,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与辽王脱脱、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帖木儿、御史大夫纽泽拥立太子阿剌吉八即皇帝位,改元‘天顺’。”
“按理说,大都一方算是叛乱方,又是仓猝起事,形势被动,可笑那倒剌沙手握玉玺,自诩正统,却优柔寡断,待他整军出征时,燕帖木儿等人早已掌控大都半月有余!”
“其后上都军与大都军鏖战数月,上都军节节败退,倒剌沙见大势已去,只得献玺请降,可怜那小皇帝阿速吉八,乱军之中生死不明,死后既无庙号也无谥号,后世仅以其年号称之为‘天顺帝’。”
朱祁镇抬起手,将飘到眼前的湿发拨到耳后,他取过一旁的丝帕,蘸了温水敷在脸上,喉间发出一声舒适的叹息,仿佛世间纷扰都抵不过这一方温水的慰藉。
伯颜帖木儿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纵观两都之战,泰定帝之子与元武宗之子,皆是元世祖血脉,泰定帝系元世祖长子甘麻剌一脉,而元武宗则是元世祖次子答剌麻八剌子孙,二帝血统本无高下之分!”
“上都一方坏就坏在倒剌沙瞻前顾后,摇摆不定,一误在拖延立君,徒留口实,二误在举兵迟缓,上都军虽有陕西行省呼应,奈何大都军已尽得中原腹地,又有京杭运河昼夜不息,将东南膏腴之地与大都血脉相连。”
“大都军一面死守潼关天险,一面迎图帖睦尔自襄阳北上,更不惜向商贾举债筹饷,聚湖广精兵、江浙军械、河南粮秣,而上都军地处朔漠,本就物资匮乏,一旦粮道被断,岂有不败之理?”
“那阿速吉八被拥立为帝时尚不满九岁,对权臣专政无能为力倒也罢了,可陛下御极多年,难道就不懂‘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的道理?”
“待郕王借御虏之名黄袍加身,二帝并立,这天下便要重现当年两都对峙之局面,难道陛下就甘心作了那死后连庙号都不配有的‘天顺帝’吗?”
朱祁镇揭下覆在面上的丝帕,水珠顺着他的下颌滑落,他若有所思地摩挲着帕子上精致的纹路,沉吟道,“朕觉得……”
伯颜帖木儿立即倾身上前,眼中燃起希望的火光,连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
未料皇帝却续道,“还是该再派一拨使者进京报信。”
伯颜帖木儿顿时像被抽干了力气般,魁梧的身躯猛地一晃,扶着浴桶边缘才勉强站稳,他不可置信地盯着皇帝,张了张嘴,却终究没能吐出一个字来。
朱祁镇不紧不慢地掬起一捧温水淋在肩上,从容分析道,“这第一回,朕遣袁彬赴怀来卫讨赏,未入京畿,母后殿下深居宫中,难明就里,只能听凭朝臣揣度,自然便将事态想得严重了。”
“第二回,朕亲书手诏,欲经杨洪递送,然《大明律》明文规定,‘若亲王所封地面有警,调兵已有定制。其余上司及大臣将文书调遣将士提拨军马者,非奉御宝圣旨,不得擅离信地。若军官有改除别职,或犯罪取发,如无奏奉圣旨,亦不许擅动,违者罪亦如之’。”
“杨洪恪守律法,不敢擅离信地,他本人不得入京,隔空传信难免令人生疑,遥隔千山万水,朝中疑为伪诏,亦是常理。”
“故而这一回,朕须得遣心腹直入京师与紫禁城,面见母后陈情,也先太师送朕返京之心至诚,何须另立郕王?”
伯颜帖木儿眼神陡然转冷,“陛下莫非以为,是有人刻意阻断消息,才让郕王有机可乘?”
朱祁镇不以为意地轻笑一声,“朕不过是顺着你方才说的‘两都之战’往下推想罢了,昔年燕帖木儿拥立元武宗后人,本为推行汉制,而既要汉化,自然要遵循嫡长继承之制。”
“故而大都军取胜后,元文宗图帖睦尔虽先即位,却仍按礼法迎立长兄和世㻋为帝,是为元明宗,元明宗在漠北和宁即位后,元文宗才遣燕帖木儿率百官奉玉玺北上,自己则屈居‘皇太弟’之位。”
“可待到元明宗驾临王忽察都,兄弟相见,欢宴之后,不过数日,燕帖木儿便毒杀元明宗,助元文宗在上都重登大宝。”
朱祁镇从浴桶中直起身来,“倘或郕王当真觊觎帝位,此番朕遣使入京,他定会不择手段地百般阻挠,若是使者在京中遭遇不测,或是有去无回,方能坐实郕王包藏祸心,证明于谦欲效燕帖木儿之故事!”
“否则,单凭你三言两语的挑唆,就要朕相信朕的亲弟弟要同朕上演‘两都之战’?就要朕相信朕在将来会变成那‘天顺帝’?朕还不至于这般昏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