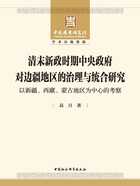
绪论
一 研究思路
(一)由差序格局到等序排列——清朝疆域形态变迁与统合方式变革
历代中原王朝通过文化认同建立王朝认同,长江黄河流域既是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文化影响力和政治统驭力均呈现由中心到边缘的衰减态势,故而即使西汉和唐这样的强盛王朝也未能将北方草原地区纳入王朝疆域,未能将游牧民族变为王朝臣民。总体而言,由中心到边缘的差序格局是中原王朝疆域的基本特征。清朝定祚中原后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原王朝的疆域形态。一方面,清朝无法像其他中原王朝一样直接通过儒家义理构建统治合法性,存在从接受到被认可的过程。从清末革命派的宣传口号来看,终清一代,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并未得到疆域内所有民众的认可。此点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汉文化的中国与大一统王朝的中国,这原先在中原王朝不成问题的‘中国’认同,却在少数民族当政的清代,撕裂为两个‘中国’之间的紧张”。[1]另一方面,清朝作为边疆民族政权,保留有自身的独特文化特征,对“夷夏之辨”的理解不同于中原王朝,比如,清初多尔衮对《春秋》中“尊王攘夷”的理解明显倾向于“尊王”,即更看重通过绝对国力扩展疆域,而非通过文化辐射力在中心疆域以外扩展外缘。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所追求的大一统疆域就完全不同于秦始皇、西汉、唐朝的大一统。秦始皇的大一统的表现形式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基础是统治族群的相对单一性。西汉、唐朝虽然不同程度上将边疆族群纳入版图,但仅以羁縻体制治之,并未实现有效治理。而清朝早在入关前即通过联姻等方式与蒙古诸部实现联盟,入关后虽然区别对待汉地行省和边疆藩部,但与以往中原王朝不同的是,无论是通过儒家伦理统治汉地行省,还是通过宗教等手段控驭蒙藏,抑或假手土司、伯克等对新疆、川边施行间接治理,清朝对疆域各组成部分的治权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在疆域内部,清朝也彻底改变了中原王朝疆域的差序格局,虽仍有中心与边陲之分,但就治理效能而言,边疆与中原并列,呈现出等序排列的结构特征。
清朝的大一统是多民族的多元一统,多元一统的基础是构建王朝认同途径的多元。清朝皇帝既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蒙古诸部的大可汗,还是藏人的文殊菩萨。无论哪种认同,核心均是以王权认同为表象的政治认同。此种政治认同具有同一性,但在同一的政治认同之下,是多元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治理方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此种认同与清朝的国力互为表里,也与清朝的国力正向相关。国力强则认同强,国力弱则认同弱。清末国力式微,加之列强不断向边疆地区进行势力渗透,直接造成传统边疆藩部地区对清朝的政治认同弱化,进而引发边疆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此种认同弱化与多元疆域构造关系密切。疆域中的各元与王权之间产生垂直的认同和统属关系,但各元之间差别巨大,彼此分割,王权式微必然加速各元的独立倾向。不得不说,这是清朝多元疆域的致命弱点。对此,清朝重建认同的方式是改造多元构造,努力实现疆域内的同质,具体表现就是实行新政改革。
迨至清末,大一统的治疆理念和疆域形态已不能适应近代出现的新情况,一统的局面受到挑战。从中原来看,清朝统治二百年间积累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在王朝统治者与列强的交涉所表现出来的腐败无能面前被极度放大,吏治腐败,鸦片流毒及咸同以后军政财政权力的下移,地方势力的坐大,引起中央权威的衰落。
清朝为了重新实现大一统,试图通过新政改革改变政治多样性,实现治理方式的整齐划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比照的并不是汉唐等中原王朝,即并没有纠缠于用接受儒家义理的程度来对抗部分汉人对其统治地位的质疑,而是将西方列强的国家政制作为改革的动力和参照,试图通过变革治理理念,改革治理体系,避免疆域因内部的多样性而分裂。就边疆治理而言,清末边疆新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颠覆,而清朝之所以要放弃在清初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究其原因,应有两点:一是边疆客观形势说明清初的治理方式已经失效,二是统治者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
就边疆形势而言,1840年以降,打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旗号的西方列强不断对边疆地区进行利益渗透,诱导当地族群脱离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原本就处于清朝疆域的外层,当地族群与满族统治层之间只是利益或实力的妥协,一旦内部的利益或实力牵制变弱,或外部出现新的利益诱体,先前王朝营造的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就会被削弱,这些地区对于王朝统治的认同也会减弱。因此,为达到重新统合疆域的目的,清王朝只有重新树立非种族性的、均质地施于全部疆域的、能够得到各民族认同的政治权威,对王朝政制架构及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机制进行深度变革,将统一的国家权力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号。清王朝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颠覆传统体制的新政改革。
就统治者的心态而言,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改革心态,二是对边疆地区的认知。清廷发布的新政上谕最能体现其彼时的改革心态。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2]可见,清廷主观上已具有改革意识,并将改革视为正常的治理手段。新政上谕很大程度上是清廷为改革寻找法理依据的方式。同时,清廷通过发布新政上谕将新政改革区别于洋务运动和康梁变法,称洋务运动只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康梁变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言下之意,只有清廷自己主导的改革才具有合法性和实效性。
关于对边疆地区的认知,学部审定的教材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学部审定满蒙新藏述略》虽为金钟麟个人著述,但经学部认可公开印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官方观点。[3]对于传统边疆藩部地区,该书称“初改行省设州县时,每县本有官设书塾,教回人以汉文汉语,奈回民不愿入塾,仍喜读回文,每晚诵经不辍。隶版图者百余年而迷信之性质不化,不得谓非教养之未至也”[4]。“藏民至愚,迫于准噶尔,扰于廓尔喀,皆当中国盛时,天戈即为扫荡,见诱于俄,败挫于英,我中国方重睦邻,而达赖、班禅亦皆仓皇无计,所谓神圣之域者阗然无灵,则数百年来奔走数万里尊严崇奉坐床之拜固无异于木偶之诬,以迷信不迫之人民而欲存于竞争世界,不亦难哉,我中国睦邻以治其标,宜急筹固圉以治其本也。”[5]可见,该书认为需要通过改革加强对新疆、西藏的统治,[6]这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明清朝希冀通过变革统合方式改变疆域的多元形态,促进整个疆域的均质化。
(二)边疆新政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
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想象即“中国之中国”。明中叶以降,中外交流加深,朝贡体系趋于稳定,中国历史遂进入“亚洲之中国”阶段。清晚期开始,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逐渐成为彼时政府改革的目标、时人批判政府的标尺,中国也开始真正与世界交织在一起,中国历史也进入“世界之中国”阶段。这个过程也就是列文森所讲的从天下到万国的过程,即中国逐渐脱离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被迫面对并参与到万国并立的国际秩序中。在三阶段的递进演变过程中,清末新政十年是关键时期。十年中,清政府通过实施新政改革,将西方作为参照系,颠覆传统体制,是中国真正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的开端。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民族国家体制定性为清朝仿照的对象。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清末新政是在现代化招牌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7]此观点可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此观点符合客观历史进程。彼时西方列强已经完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国家主权和统一领土,建立起完整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同时,借由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相对于王朝国家的优势地位。近代以降,伴随中国在中西冲突中屡战屡败,此种比较优势逐渐演变为区分文野的表征,西方民族国家政制进而成为清朝趋新、趋强改革的参照目标。另外,就客观效果而言,加强疆域内各族群尤其是边疆地区族群的国家认同,是清朝在传统藩部地区施行新政的重要目的,这与民族国家特征之一——内部统一的具有高度认同的民族吻合,这也是清朝在其统治末期的重要历史贡献。尽管清朝此种努力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疆域内族群在文化、语言、治理体制等方面依然保持多元,为后来日本学者抛出“满蒙非中国论”提供了口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末十年是重新统合藩部地区,摆脱传统天下中国形象,形塑现代中国的关键时期。
但另一方面,此观点有臆测清王朝改革的主观动机之嫌。清王朝作为改革的主导者、实施者,其改革的目的只能有一个,即巩固自身统治。其主观动机是对既有政制进行改造,提高治理能力,虽已摆脱体用的纠结,但从辛亥前其抛出的皇族内阁来看,其引进的所谓“西体”的装饰作用明显大于实际作用。故而清王朝的改革虽在客观上造成国家政治架构向民族国家的靠拢,但不能由此认定其以民族国家为改革旨归。我们应区别对待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8]
清朝的大一统疆域建立在多元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之上,总体上表现为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二元分立。在边疆地区内部,清朝针对不同族群施以不同的统治秩序。清朝虽然将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差异巨大的不同族群整合在同一个统治秩序之下,但终清一代,并没有将不同族群整合为具有同一性的“国族”的主观动机。一方面,历代大一统王朝均实行多元政制,清朝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清朝追求的是疆域各组成部分对于王朝的单向认同,而各组成部分之间是否有紧密的联系并不影响王朝认同的效果和大一统疆域的构建。迨至清末,大一统的疆域形式虽然完整,但国力式微直接造成王朝认同资源趋于瓦解,大一统疆域亦有崩塌之虞。对此,清朝通过新政改革增强中央王朝对疆域各组成部分的统驭力度,变被动认同为主动树立权威。
发生在清末的以新政为表现形式的从天下中国观到统一的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过程中长时期持续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它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近代中国人对中国的多民族构成和中国版图的见解与清王朝的政治遗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联系。发生在清末边疆地区的新政改革,是清王朝在其统治行将落幕之际留给后人的重要政治遗产,其影响并未限于边疆一隅和清末一时,它对于此后中央政府治理边疆,抵制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当今边疆地区多民族和谐共处格局的形成均具有突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