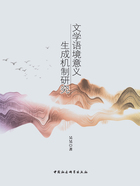
二 20世纪文学研究的语境思维变革
“语境”被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中来(作为一个新范畴,而不是传统的“上下文”),并被广泛加以运用,同样伴随着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层变革。瑞恰兹首先将“语境”引入文学文本的细读,是一种文本观念的变革;后期维特根斯坦使用“语境”概念寻求语言的新意(“意义即用法”),也是对逻辑语言观的反叛;加达默尔在肯定诠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阐释学;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的语境之客观性的怀疑,奠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卡勒和伊格尔顿从文学的语境上界定什么是文学,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文学本质的寻求模式。
语境究竟给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变革?这一问题我们尚未全面地思考和总结。文学不同层面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都发生了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和语境有密切关联,不过它们在语境思维的运用上各有侧重和选择:文学话语层面注重语境的实践性和对话性,文学阐释层面侧重语境的时空性,文学文体层面关注语境的开放性,文学历史批评层面主张语境的主观性和虚构性,文学本质层面运用语境的无限性。
(一)文学话语层面的语境视野
20世纪上半叶深受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语言学、修辞学、词汇学、文体学等众多领域的语言研究都致力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排斥日常生活的鲜活话语。在这种研究的狭隘日渐显露之时,语境以其强烈的实践性和对话性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正如克雷茨曼所说:“语词不再作为与它们的语言上下文或语境完全相分离的单位来研究。吸引着人们强烈兴趣的,毋宁说是语境本身。”[16]
1.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实践性语境思维
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前期观点的自我批判,是语言哲学研究思维变革的一个缩影。他前期信奉罗素的观点——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达到对世界的理解——企图建立晶体般纯粹的逻辑语言。这种研究自然脱离了鲜活的话语实践。而在1929年他重新研究哲学以来,则开始反省第一本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的严重错误,转向日常话语实践的研究,在语境视野之下提出“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全貌概观”“生活形式”等重要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在使用“意义”这个词时,都应该如此说明:“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17]他以“我害怕”这句话的意义为例,阐释语境对于意义的重要性。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很遗憾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还是有点害怕,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怕了。”
“我骨子里仍然害怕,但我不会对自己承认它。”
“我用种种害怕折磨我自己。”
“现在,恰恰是我应当无所畏惧的时候,我却害怕了。”
对于这里的每一个语句都有一种特定的语调、一种各自不同的语境与之相适合。……
我们问:“‘我恐惧’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说这句话时我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找不到回答或者找到一个不适当的答案。
问题是:“它出现在何种语境中?”[18]
如果缺少语境,我们无法确定“我害怕(恐惧)”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语言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能确定其意义。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视野其实是对话语实践的倾向。实践性可以说是语境在语言哲学中方法变革的重要特征。维特根斯坦开启了语言哲学对于话语实践的重视,以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进一步推崇语境意义,促成了以语境为核心概念的语用学的兴起。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研究的实践性的关注,可扩展到语言的整体和人类生活的整体,这在他的“全景概观”“生活形式”等思想中可见一斑。他认为我们无法看清字词用法的全貌,是因为我们没有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语言系统与语言的使用相分离。更进一步,他还提出“语言游戏”即为“生活形式”的一种,将语言放置于人类生活的整体中来审视。“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19]“语言游戏”这个词的用意在于突出“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20]
2.巴赫金的对话型语境思维
巴赫金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在语境方面有两个最为突出的贡献:一是将语境的视野从上下文拓展到社会语境;二是看到话语间、语境间的对话,提出对话型语境的思想。
巴赫金的语境思维是向社会生活敞开的。他不仅看到了长篇小说中某一词语的上下文,也看到了这一词语身上所散发出的社会生活的语境气味。“所有的词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代人、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每个词都散发着它那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处的语境的气味;所有词语和形式,全充满了各种意向。”[21]这和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思维大相径庭。后者割断文本与社会的联系,而巴赫金则将整个社会生活融入作品,时刻发现作品与社会的连接。通过这些连接我们可以体会到文学作品更为复杂的意味。这种向社会敞开的语境思维与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视野相同,注重和运用的是语境的实践性。
同时在语境思维上,巴赫金也保持着他的对话意识,形成了独特的“对话的语境”思想。巴赫金认为修辞学、语言学和词汇学在研究语言时所关注的语境是独白型的,没有看到仿格体、讽拟体、故事体、对话体等艺术语体中语言的双重指向。这些艺术言语“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22]小说中每段话语都具有自己的言说语境,但语境之间、话语之间并非独立。“每个人所接受的话语,都是来自他人的声音,充满他人的声音。每个人讲话,他的语境都吸收了取自他人语境的语言,吸收了渗透着他人理解的语言。”[23]我们以往关注的都是一段话语自身的语境,而忽略了话语之间的对话,或语境之间的对话。巴赫金的“对话的语境”概念提醒我们的正是语境思维这方面的疏漏。
(二)文学阐释层面的语境本体论和方法论
如果话语层面主要运用语境思维的实践性的话,那么在阐释层面语境思维的时空性备受关注。加达默尔通过树立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价值而创立现代解释学,瑞恰兹则将文本语境的时空长度无限延长,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文本解读的多义性。
1.加达默尔的解释主体语境
加达默尔的语境思维具有极强的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重新审视上。他的语境思维关注的是主体语境的时空性。
在传统解释学的观念中,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主体应该超越自身的历史语境,使自己与解释对象处于同一时代,“理解”就是要回到艺术作品原初的语境,“重建”艺术作品所属的世界。而加达默尔所批判的正是这种让解释主体背离他自身的历史性的异化的方法。
首先,解释主体自身的语境是他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不是仅凭一个态度就能脱离的,而且这个语境早已本质性地隐含在理解的全过程中。“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和前见解,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诠释学必须把那种在以往的诠释学中完全处于边缘地带的东西置于突出的地位上,这种东西就是时间距离及其对于理解的重要性。”[24]语境的时间距离是不可避免的,解释主体所处语境带来的前见也必然存在于他的理解中,而某些前见恰恰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入之见,对于理解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重建艺术作品原初的语境也是一种无效的解释行为。在加达默尔(也作伽达默尔)看来:“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25]而且他认为“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26]在加达默尔看来,艺术可以通过它的现时意义去克服时间的距离,“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27]
语境思维的时空视野不仅让加达默尔重新审视解释主体语境的价值,提出解释学的全新的方法论,也让他看到主体语境的不断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艺术的真理观和意义观提出质疑。“在艺术经验中难道不存在某种确实是与科学的真理要求不同、但同样确实也不从属于科学的真理要求的真理要求吗?”[28]艺术乃至人文科学领域的真理,不像自然科学的真理那样,能通过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获得,只能通过“体验”的方法来证明。“这里所涉及的真理(艺术的真理——引者注)并不能在一般的陈述或知识中得到证明,而是通过自身体验的直接性以及自身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而得到证明。”[29]然而体验总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因而每一次体验所获得的真理和意义都会不尽相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加达默尔才说:“我们为了理解某位思想家而试图与该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的每一次对话都是一种自身无限的谈话。一种真正的谈话就是我们在其中力图寻找‘我们的’语言——即一种共同的语言——的谈话。”[30]任何理解都是一场自身无限的谈话,让自身当前的历史存在向过去的思想开放,在当前和历史语境的相互调节中找到我们共同的语言。因而艺术的真理和意义在无限的谈话和体验中也都是永远敞开的。
加达默尔的语境思维并不限于方法论的层面,因为他赋予现代解释学的任务是本体论层面的。“哲学解释学的任务与其说是方法论的,毋宁说是本体论的。它力图阐明隐藏于各类理解现象(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理解)之后,并使理解成为并非最终由进行解释的主体支配的事件的基本条件……只有当我们使自己从充斥于近代思想中的方法主义及其关于人和传统的假定中解放出来,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才能够显现。”[31]现代解释学从本体论的层面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理解的认识,在科学和非科学的理解中发挥着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从语境思维的时空性肯定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存在的价值,是加达默尔颠覆传统观念的起点;从语境思维的时空性看到解释主体语境的不断变化,则是他敞开的真理观和意义观的逻辑基础。因此加达默尔的语境思维不仅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真理的本体论。
2.瑞恰兹和新批评的文本细读语境
瑞恰兹是最早将“语境”引入文学研究的,1936年他在《修辞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完整的“语境定理”。这一定理成为其后新批评文本细读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批评方式。瑞恰兹的语境理论主要运用的是语境无限的时空性。他将语境的所指范围从“上下文”扩展到文本出现时“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以及“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32]并且由此确定了一个词语的意义与语境的节略形式有关,在语境中,一个词承担了几个角色的职责,因此这些角色就可以不必出现。“当发生节略时,这个符号或者这个词——具有表示特性功能的项目——就表示了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那些部分。”[33]
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那些部分。但因为语境的时空不受限制,无比多变丰富,所以词语的意义自然出现复义现象。“意义的语境理论将使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最大的范围里遇到复义现象;那些精妙复杂的复义现象比比皆是……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做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34]因而文学语体中的语境的功能由日常语体中的确定意义功能变为丰富意义,即复义的功能。
瑞恰兹给语境下了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35]运用这一语境定理来分析文本,意味着要找到一系列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事件及条件来剖析文本中的复义现象。比如莎士比亚的一句诗:“唱诗坛成了废墟,不久前鸟儿欢唱其上。”这句诗没有双关语,没有双重句法,也没有暧昧的感情,原本意义明了。但是燕卜荪深究其中比喻的意义,即唱诗坛和树林之间、唱诗人与鸟儿之间构成比喻的原因,语境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便呈现出来:“因为坍塌的唱诗台是唱歌的地方;因为唱诗台上的人要坐成一排;因为它是木制的,且雕成节状;因为它们曾被酷似森林的建筑材料复(应为覆)盖,建筑物的彩色玻璃和里面的绘画就象(像)绿叶和鲜花;因为它的周围再没有善男信女,只有灰色的断壁象(像)冬日的天空;因为唱诗男童的严肃而可爱的神情跟莎翁对十四行诗的感受非常合拍。还有许多其他社会、历史原因(如新教徒摧毁寺院、对清教主义的畏惧等)……”[36]燕卜荪用来分析比喻的这些原因,既包括文本出现时“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也包括“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在批评家分析诗歌语言时再现,使原本意义清晰的诗句变得意义朦胧。
新批评派其他成员的诗歌理论和批评也借鉴瑞恰兹的语境理论。
布鲁克斯这样界定反讽:“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37]而且这种被语境修饰的反讽在诗歌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它的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38]他相信“语境赋予特殊的字眼、意象或陈述语以意义。如此充满意义的意象就成为象征;如此充满意义的陈述语就成为戏剧性发言。”[39]因为语境的赋予,所以“不”重复五遍成了《李尔王》中含义最沉痛的一句。维姆萨特则视语境为隐喻的发生结构和活力源泉。隐喻的意义是由独立的喻体与喻旨在新的语境中受到扭曲而产生。“只有当隐喻脱离‘语境’被随便地重复滥用时,它们才会容易变得简单化,囿于字面意义,变成陈词滥调。”[40]语境思维可以说是贯穿新批评众多概念和批评实践的一根红线,毕竟任何一种修辞都离不开语境的支持。
语境无限的时空性,在瑞恰兹的文学语义学和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实践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加达默尔是运用语境思维的时空性来确立一种新的解释观和方法论,那么瑞恰兹和新批评则是将语境无限的时空性切实地运用于文本细读实践,并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方法。
(三)文学文体层面的语境化研究倾向
文体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呈现出从文本主义到语境主义的发展趋势。卢森堡大学的雅各布·韦伯在《文体学读者:从雅各布森到现在》中直接言明这一语境化倾向:“这一时期文体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语境化倾向。在主流语言学中受到相似潮流的影响,一种新的发展势头也在积聚,随着语用学、话语分析等分支学科的发展,语境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41]语境化的文体研究关注的不是文本内部,也不是读者的意见,而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效果。而且意义和文体效果不再是确定的、稳定的,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实现于读者的阅读中,被视为作者和作者创作的语境、文本的语境、读者和读者接受的语境之间相互对话的结果。
韦伯进一步提出可以把文体分析的这种语境化运动看作文本的语境逐渐扩大的过程,就像围绕文本的一系列同心圆的扩展轨迹。他列举了扩展这个语境同心圆的诸多文体学家及其理论,如以玛丽·路易·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为代表的言语行为文体学(speech-act stylistcs),以米克·肖特(Mick Short)为代表的语言语用学[42](Linguistic pragmatics),以罗杰·福勒(Roger Fowler)为代表的批评文体学(Critical-stylistic),以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为代表的女性文体学(Feminist stylistcs),以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的关联理论,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off)的认知语言学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等。
众多文体学流派均表现出文体研究的语境化倾向,因此很多文体学家,如布拉福德和萨拉·米尔斯,赋予这些流派一个统称——语境(主义)文体学。
布拉福德(Richard Bradford)在《文体学》中将20世纪的众多现代批评理论分为文本主义文体学和语境主义文体学两种。语境主义文体学的流派众多,研究方法甚至彼此迥异,但它们都共同强调文学文体的形成受其语境的影响。布拉福德对语境所涉及的要素提出自己的看法:“(1)读者的能力和性格;(2)主宰语篇(包括文学语篇)的主要社会文化力量;(3)我们借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语言和非语言、文学和非文学)的符号指称系统。”[43]基于这个标准,布拉福德将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福勒的批评语言学、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米尔斯的女性主义文体学以及功能文体学等,都归入语境主义文体学的范畴。
他详细介绍了罗兰·巴尔特的颠覆性的文体观念。从修辞学到文本主义文体学,西方学者对“文体”尤其是文学文体一直抱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它能把语言从其实用和功能性角色中脱离出来,引向自我指涉的领域。因此我们一直将文体和语言相区别,认为文体就是修辞,就是自我指涉的文学装备,而语言就是一种发挥实用性用于交流的符号手段。而罗兰·巴尔特则质疑这种传统的文体观念,他将这种任意的自我指涉系统视为所有话语类型的条件。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推翻这种将文体和语言相区别的传统观念。在《写作的零度》中他尤为关注同时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体。这些后现代作家在做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既使用文学文体去消除创作中外界的语境因素,也从非文学话语的语境中提取同时代世界的广泛的新奇的文体。巴尔特断定这种现代的创作方式是一种零度的写作,一种纯粹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中语言的文体的和功能的两种状态是不断变化的。
不仅后现代作家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创作方式,布拉福德认为所有的文学文体都表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因而提出“双重模式”(the double pattern)的概念。这一概念关注的是诗的两种相异的特征,一种是独属于诗歌写作的特征;另一种是诗分享其他话语的特征。相似的,小说的文体也是一方面彰显着独特的虚拟叙事风格;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非文学风格,这两者的张力关系也构成一种双重模式。文本主义文体学和语境主义文体学都意识到了双重模式的张力,但他们各自选择了双重模式的两极。文本主义者关注文学不同于普通话语的自我风格,而语境主义者则在更广阔的句法、词汇、政治、历史、性别、文学等语境中审视文学的构成特征。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布拉福德把罗兰·巴尔特、费什、福勒等人列为语境主义者,而把燕卜荪、布鲁克斯、雅各布森视为文本主义者。
从布拉福德对语境主义文体学的界定来看,语境主义在文体学中意味着一种区别于封闭的文本主义的开放的文体研究方法——结合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文学文体,不再强调文学文体区别于普通话语文体的独特性,而是试图寻找文学文体与普通话语文体的共同性。文体学研究这种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注,是20世纪现代批评理论发展的整体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替代沉寂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成为主流理论——在文体研究领域的表现。
英国文体学家萨拉·米尔斯尝试界定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语境文体学”(contextualized stylistics),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体学的结合能够克服在传统文体学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语境文体学彻底脱离了传统文体学——从文本内部批评转移到更为关注决定文本内部要素的文本外部因素。这并不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重新发现,语境文体学对语境的关注采用的是一种更有趣的理论研究方法。它强调词汇及其与语境相互作用的方式,这能够帮助读者避免传统文学批评中某些过于笼统的因果假设。”[44]
米尔斯将传统语篇文体学和语境文体学中的两种语境模式加以对比。传统语篇文体学中的语境模式较为单一:
社会历史背景—作者—文本—读者
而语境文体学中的语境模式更为复杂:

图1 语境文体学的语境模式[45]
相比传统的语境模式,米尔斯指出语境文体学的语境模式具有两大优势:第一,文本的创作和接受都被纳入语境的一部分,而不像传统语境模式那样仅仅强调文本的创作。第二,读者的作用被凸显出来,读者不仅受文本言说的影响,也是文本意义生成的积极参与者。这个模式比传统模式更复杂,因为考虑到文本与其语境间的互动,即文本受到创作和接受时诸多力量的影响。因而想要像传统文体批评那样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将更为困难。相反,这个模式将推导出一个更适中的说法,例如文本向读者言说的方式以及读者对抗这种言说的限度。虽然米尔斯的语境文体学针对女性主义文体研究而发声,但显然她对语境的理解比布拉福德更为广泛。
从各个语境主义文体学流派来看,他们引入文本之外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信息,将文学话语与一般话语的文体研究打通,借助语境的开放性彻底打破了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文本主义研究模式。
(四)文学历史批评层面的语境怀疑论
20世纪末,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对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驳斥某些文学理论家抛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强调必须将作家的意识或文本融入它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另一个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更进一步地探讨文本和语境的关系问题。文本和语境的关系是自黑格尔以来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怀特对这两者的客观性均提出质疑:历史文本的权威和物质性消失了,稳固于言辞的历史语境也消失了,文本和语境的关系曾经是历史研究无须审视的前提,如今却变得不可判定、晦涩难懂和不可信。这两者关系的变化为思想史家开拓了一番新的思维景象,让他们对历史档案的态度不再是武断的分析,而转变为谨慎的审视和对话。
在文学理论家的眼中,历史一直是现实主义再现的不容置疑的原型,其语境也具有一种抽象性和不可接近性,但怀特却截然相反地向我们指出历史经典具有本质上的文学性。“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46]因此,稳固于这些文本中的历史语境也成为虚构的产物。“历史语境的这种假定的具体性和可接近性,即文学学者所研究的文本的这些语境,本身就是研究语境的历史学家们的虚构能力的产物。”[47]那么,用于研究文学作品的历史语境本身也成了需要识别的对象。
想要识别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的虚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成分,怀特认为我们首先要纠正的是一种错觉——历史文本直接指涉事物。因受到意识形态的歪曲,历史文本并不直接指涉事物,需要我们借用符号学的方法来揭示其中客观的部分。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者,怀特推崇巴尔特的方法,建议仿照《S/Z》一书的方式,从书的题目、编者前言开始对文本成分的修辞性进行描述,然后进一步解释代码转换的特征,最后再详细剖析特殊段落的元语言学成分。客观的历史语境只有通过这样的文本分析才能够被阐明。
除了历史语境,怀特还在历史分析的范式研究中概括出一种语境论(也译为情境论)的论证形式。在《元史学》中文版的导言中,怀特把历史著述理论区分为五种模式: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每种模式都各有侧重,其中形式论证模式关注解释的外在形式,怀特又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将形式论证模式区分出四种范式——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形式。语境论是对其他三者的调和,它避免了形式论的极端分散的倾向,也避免了有机论和机械论的抽象倾向。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怀特这样描述:“语境论模式则通过把事件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环境’当中来解释事件。这涉及事件与周围历史空间的关系,与这个空间内其他事件的关系,以及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环境里,历史动作者与动因之间的互动关系。”[48]但怀特对这种语境论的范式也持有怀疑态度。“情境论者探索历史解释问题,可以看成是两种冲动的结合,一种是形式论背后的分散性冲动,另一种是有机论背后的整合性冲动。但事实上,一个有关真理、解释和确证的情境论概念,在它对史学家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中,似乎都过于平庸了。”[49]
无论在传统的历史语境还是语境论解释范式上,怀特都报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源于他将历史文本视为具有“文学性”的基本观点。他引领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反思历史文本及其语境的客观性,揭示出历史文本和语境的虚构性、主观性,并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一种解决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怀特是一个语境客观性的怀疑论者,他注重的是语境的主观性和虚构性。
(五)文学本质层面的语境决定论
在文学的本质层面上,语境也越来越被重视,在乔纳森·卡勒和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念中,语境是决定什么是文学、决定文学意义的关键要素。
在寻求文学本质的道路上,我们历来采用一种在文学内部寻找共同特征的方式。卡勒总结理论界从这种视角出发已得出的结论: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语言的综合、虚构、审美对象、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建构。然而,“这每一个被认定的文学的重要特点都不是界定特征,因为在其他类型的语言运用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特征。”[50]这是因为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表现特征:“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相同之处,而与那些公认的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51]
卡勒、伊格尔顿都援引“杂草”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弊端。文学就像杂草一样,很难找到所谓的“杂草状态”——所有杂草共有的那些特征。因为杂草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主人不愿在其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因此卡勒建议我们与其寻找杂草状态,不如做些历史的、社会的或者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换句话说,卡勒在这种传统内部视角之外辟出另外一种回答“文学是什么”的视角和方式。“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作程式的产物,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52]把文学看作程式的产物或某种关注的结果,而并非将其理解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特点的语言,这是另一种探寻什么是文学的外部视角。那么从外部视角来思考是什么让一段文本引起我们的关注?答案就是语境。
卡勒认为有时研读对象具有成为文学作品的特点,但也有时是文学语境使我们把它看作文学作品。比如在什么地方读到一段文本。“大多数情况下是那种可以把一些文字定义为文学的语境使读者把这些文字看作文学的,比如他们在一本诗集、一份杂志的某一部分,或者图书馆和书店里看到的那些东西。”[53]卡勒甚至给出了这样一种文学的定义:“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54]
而且卡勒在内部视角中也引入语境理论,他提出文学属性的确定,与其从其他话语语境中分离出来有关,一旦分离它就构成了文学自身独特的语境,能够引发关注。“当语言脱离了其他语境,超越了其他目的时,它就可以被解读成文学。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脱离了其他功能和目的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关注。”[55]这些语境使读者相信文学作品与其他文本不同,相信这段文本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因为“文学作品经过了选择过程,也就是说,经过了出版、评论和再版的过程。读者是因为确信别人已经发现这些作品构思巧妙、‘值得一读’才去阅读它的”[56]。
伊格尔顿除了将文学喻为杂草,也将之比作游戏。他认为从文学文本中分离出其内在特征的传统做法,就像试图确定所有游戏都具有同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提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文学的本质。“要从所有形形色色成为‘文学’的文本中,将某些内在的特征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事实上,这就象试图确定所有的游戏都共同具有某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57]伊格尔顿进一步提出:“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获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自己的。从这一点讲,后天远比先天更为重要。重要的可能不是你来自何处,而是人们如何看待你。假如人们断定你是文学,那么,你似乎就是文学,根本不考虑你认为自己是什么。”[58]
所以卡勒和伊格尔顿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都是主张语境决定论的。他们把文本隶属的书籍属性(诗集、杂志)、地理位置(图书馆、书店)、出版、文化权威的评价等外部因素都视为可以决定文学的因素。而且伊格尔顿在文学本质问题上比卡勒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换句话说,他否定文学的本质,且在两种视角上极力推崇后者,即语境的力量,即便他没有直接运用语境一词。而卡勒并不绝对否定文学本质的传统内部视角。虽然他认为我们过去从传统视角所提出的文学特点并不是界定特征,但他也明确表示内部的传统视角和外部的语境视角截然不同,不论哪种视角都不能包容另一种而成为一个综合全面的观点。
语境决定论的文学观自然会带来意义的语境决定论。卡勒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一定要一个总的原则或者公式的话,或许可以说,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因为语境包括语言规则、作者和读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象得出的相关的东西。”[59]然而卡勒给这个公式加上一个条件,即“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60]。
卡勒的这个公式充分运用了语境的无限性。在他看来文本的意义解读是没有限定的,可能会与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关,而只有不加限定的语境才能囊括所有的相关因素。从这个角度,卡勒认为:“可以把理论话语引起的关于文学解读的主要变迁理解为语境的扩大,或者叫语境的再描述的结果。”[61]并且在理论话语的压力下,意义将永远变化不定。
伊格尔顿对于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评定的阐述,就像是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卡勒意义公式的详解。尽管人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评价同一部作品,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评价“同一部”作品。“‘我们的’荷马并非中世纪的荷马,同样,‘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说得恰当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目的塑造‘不同的’荷马与莎士比亚……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由阅读它们的社会‘再创造’的。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在阅读时不是被‘再创造’的。”[62]文学的意义、价值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伊格尔顿也如卡勒那样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永远变化不定的,不同的是卡勒没有限定决定意义的因素,而他强调的是读者接受的语境。
综上所述,文学的话语、阐释、文体、历史批评和本质层面,都因为引入语境理论而引起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革。诸位学者虽然对语境思维特性的运用各有侧重,但大多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语境决定论者。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即在语境中的具体用法,加达默尔提出解释主体语境的决定性,新批评将语境视为文本复义、隐喻、张力的基础,语境主义文体学认为文体的形成与其语境有关,卡勒和伊格尔顿更是明确地主张语境决定了什么是文学、决定了文学的意义。
[1]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 参见[美]戴维·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洪国定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页。
[4]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页。
[5]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6]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7] 王德春:《修辞学探索》,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8] 张志公:《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214页。
[9] B.Malinowski,“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in C.K.Ogden and I.A. 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Supplements,1923,pp.306-309.
[10] [日]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4页。
[11] Richard H.Schlagel,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cience,New York:Paragon House,Introduction,1986.
[12] 参见[美]戴维·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洪定国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3] 郭贵春:《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成素梅、郭贵春:《语境论的真理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5] 殷杰:《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
[16] Kretzmann,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6.
[17]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页。
[18]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286页。
[19]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20]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21] [苏]巴赫金:《长篇小说话语》,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2] [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23] [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24]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5]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26]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27]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28]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29]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页。
[30]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01页。
[31] 编者导言,载[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2] [英]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33] [英]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34] [英]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35] [英]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36] [英]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周邦宪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7] [美]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物社2001年版,第379页。
[38] [美]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物社2001年版,第380页。
[39] [美]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物社2001年版,第379页。
[40] [美]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物社2001年版,第405页。
[41] Jean Jacques Weber,“Towards contextualized stylistics:An overview”,in Jean Jacques Weber,ed.,The Stylistics Reader:From Roman Jakobson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Arnold,1996,p.3.
[42] 语言语用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分裂为社会语用学和认知语用学。
[43] Richard Bradford,Stylistics,New York:Routledge,1997,p.73.
[44] Sara Mills,“Knowing Your Place:a Marxist Feminist Stylistic Analysis”,in Michael Toolan,ed.,Language,Text and Context:Essays in Stylis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82.
[45] Sara Mills,“Knowing Your Place:a Marxist Feminist Stylistic Analysis”,in Michael Toolan,ed.,Language,Text and Context:Essays in Stylis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84.
[46] 中译本前言,载[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7]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1页。
[48]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9]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50]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51]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52]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53]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54]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55]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56]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57]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58]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59]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0]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61]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62]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