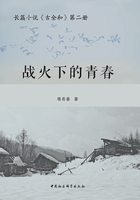
第8章
胡大珂闷坐在堂屋灶前的那张两头儿向上翘起的小板凳儿上,那是他的恩师留给他的宝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双臂抱在胸前,想着一家的生计,不时轻轻地叹息。他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发愁过。外面天寒地冻,什么活路儿都没有,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处去使。房东曹老二满口答应说开春儿他可以到他家去扛活,根儿可以给他家放猪。而这里到阳历五月初头儿才开犁下种,要等四个月才能拿到劳金。赵凤山说明年开春儿这里要盖很多房子,会有铁匠活儿可干,不过那也是四个多月以后的事。远水解不了近渴,难熬的春三月怎么过呀!这会儿唯一的出路儿是跟上赵凤山下乡去贩私粮挣钱。
赵凤山,山东菏泽人,有胆有识,急公好义,有一身好武艺,从不叫苦犯愁。他是最早来拜访胡大珂的男人。有些人相处多年,彼此也无恩怨,却总是人心隔肚皮,不能知心,而胡大珂和赵凤山是一见如故。胡大珂感谢赵凤山的帮衬,但是在是否下乡背粮这件事上,他游移不定。他知道,日本人对所谓满洲人实行粮食配给制。所谓满洲人,也就是中国人,只准吃磨过一两遍的粗糙发涩的红虾虾的高粱米和难咽难拉的橡子面儿,其他粮食不许买卖。买卖大米、白面和鸡蛋叫“国事犯”;贩卖小米儿、大豆、玉米等杂粮叫“经济犯”。可是老百姓还是要吃杂粮。关里来的成年人,特别是山东的老年人,初来乍到,几乎都不习惯吃高粱米。奶奶吃了高粱米就心口疼。而且大米、白面、杂粮、鸡蛋人们也是要吃的。江城有数以万计的山东人。他们把山东煎饼带到了这里。这里到处是门前飘动着上书“山东大煎饼”的白布黑字的幌子的煎饼铺。它们卖高粱米煎饼,也卖小米儿煎饼,制作小米儿煎饼的原料就是黄豆和小米儿,而黄豆和小米儿就来自粮食贩子。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私粮”挣钱谋生养家,就成了那些走投无路的穷苦人的一条生路。贩私粮本儿小利大,但是很危险。一旦落到警察手中就会血本无归,更可怕的是人会被发往煤矿去当劳工,而当劳工就是下地狱,几乎是有去无回!现在摆在胡大珂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火坑,他不跳他一家老小儿就得挨饿,等死。
胡大珂信任赵凤山,反复地考虑过赵凤山的建议,觉得贩私粮见效快,跑一趟就能挣出一家人十几天的口粮。不过这是拿命去换粮,跑一趟,要在零下40度的茫茫的雪原上,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下,奔波一百几十里路,一旦落到警察手里,性命难保。如今弟弟不在了,大舅哥和妹妹两家远在山东,要是自己有个闪失,老娘怎么办?秀姑和根儿怎么办?而要是不去呢,一家老小儿眼前就得挨饿,胡大珂一时拿不定主意,而又不能和家里的人商量。
“根儿他爹,你不用发愁。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奶奶眼见儿子愁得连饭都吃不下,怕他会愁出病来。“娘什么都不怕,如今还能帮衬着你们过日子。实在无路可走了,俺就再拖上棍子出去讨饭!”
根儿说道:“俺和奶奶一起去,去给奶奶打狗!”
胡大珂听奶奶和儿子这样说,想起老娘当年为了把年幼的姑姑和自己兄弟姐妹四人养大成人所受的苦难和羞辱,忍不住一阵心酸,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他想说点儿宽慰和感激老人的话,可是想说的话却都噎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秀姑急忙拦住奶奶,说道:“娘,俺们不能再让你老人家受累啦!”
奶奶睁开眼睛心疼地看看儿孙,后悔自己在这年关时候说出了让儿孙们难受的话。原本想宽宽儿子和媳妇儿的心,反倒让他们伤心流泪。
这时北面响起了敲门声,有人叫道:“胡大哥在家吗?”
胡大珂听出是赵凤山,急忙站起身,转身打开屋门,把赵凤山让进来。
秀姑笑着从炕沿儿上站起来,让出地方儿给赵凤山坐。
赵凤山四年前带领妻子和女儿来到本市。先在潘家油坊大财主潘老三家扛过一年长活,后来又到炮手屯杨大琢磨家当了一年的把头。从前年冬天起,夏秋两季干瓦匠活儿,入冬后就伙同一些山东老乡下乡贩私粮。
赵凤山说:“胡大哥,怎么样,去吗?”然后又说,“去吧,俺保驾。”
胡大珂想,下乡背粮的穷哥们儿谁不是舍命去挣口饭吃!为了让老娘和妻儿吃上饱饭,就是去冒天大的风险他也心甘情愿,一拍大腿,断然说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