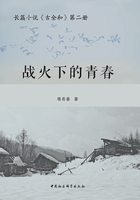
第12章
秀姑萌生下乡背粮的念头儿并非偶然。胡大珂一家来到宋家屯镇第一个外出谋生的不是胡大珂,而是秀姑。她在来到山东庄的第二天就忙不迭地进了日本人丸山氏在本镇开设的灭蝇水公司洗涮玻璃瓶子。在这里打工的全是外地来的女工儿,主要是山东人,多数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也有少数中年妇女。她们即使在三九天也在露天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洗涮玻璃瓶子的水泥池子里的水时刻在结冰,水面上不时浮起针一样的丝丝冰凌,女工们要一边清理水池子水面上的冰凌,一边工作,公司的要求苛刻,百般挑剔,而报酬极低,每洗涮一个瓶子,里里外外验收合格儿后才只给一分钱,多数女工一天挣不到一块钱。失手损坏了玻璃瓶子要扣工资赔偿。秀姑全天猫在水池子边上苦干,还挣不出一家人的饭钱。这份儿工作好找,可是没有谁能坚持干,干得长久,人员走马灯似的轮换,没有人能坚持连续干上半个月。秀姑在上工的头一天双手和手臂就冻伤了,几天之后伤处开始化脓,痛痒难忍,离开了那里,一家人又面临绝路,胡大珂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冒险下乡去背粮。可是秀姑又忍受不了彻夜为丈夫的安危担忧的痛苦的折磨,害怕他被抓了劳工,一去无回。她想,她的老哥哥和小姑子两家都在千里之外,他们的姑姑一家远在黑龙江的深山老林,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和自己一样穷的叔伯哥哥,丈夫一旦有个好歹,一家人就完了。昨天夜里,她无数次地想象过丈夫在漆黑寒冷的雪地里奔波,和他可能遭遇的种种不幸,寻思着摆脱这种痛苦和不幸的出路,想到了自己下乡背粮的这个主意。她不怕抓劳工,有一双和男人一样的大脚,力气比丈夫大,身上有功夫,遭遇警察动起手来也不会吃亏。
胡大珂犹豫再三,决定再下乡背几趟,积攒下一些粮食,好让一家人平安地混过这个冬春。可是奶奶和秀姑都不同意他去。秀姑坚持说她要去,一再对奶奶和丈夫述说她去背粮的好处。奶奶和胡大珂虽然觉得她说得有理,可还是不同意她去。奶奶想,眼下冷冬数九,要是秀姑出点儿意外,伤了,残了,冻死在野外……她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孙子?再说,一个妇道人家,和一群大老爷们儿白天黑夜地在一起滚,以后说起来也不好听啊。根儿更是又哭又嚎,死活不肯放他娘走,还说他要跟他爹一起下乡背粮。一家人齐声反对,秀姑只好暂时放弃下乡背粮的打算。
今天是个晴天。隔两天就是大年初一了。一家人说好同意胡大珂再次下乡背粮。这回根儿没闹着要去,他说孙孝友叔叔家的道士找他有事,饭后就出去了。
午饭后,赵凤山、胡大珂等一行男女老少12个人,把背粮食用的口袋和绳子裹缠在身上,带着饭后的余温,迎着刺骨的西北风,说说笑笑地上了路。他们有的是三四年前来到这里的,有的是不久前才来到这里的。可是他们中间没有谁混上一身像样儿的御寒的行头,穿的还都是从山东、河南、河北老家带来的那些不知道拆洗过多少遍的并不保暖的棉袄棉裤。他们在老家能够靠着这些行头勉强过冬,而根本不能靠它们抵挡松辽大地上寒冬腊月刀剑一般的西北风,眨眼间他们身上的体温就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这时,他们就像赤裸着身子,迎着冰冷的寒风在雪地里行走。仅只一两袋烟的光景,他们的双手就冻木了。接着,面部的肌肉和五官也冻僵了。与此同时,他们的思路儿也渐渐变得狭窄了,头脑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所有人的脸都不再能够自如地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孙孝友不满11周岁的儿子道士只穿了一件棉袄,下身穿的还是不知补过多少回的两条套在一起的夹裤,脚上穿的是家做的布棉鞋,他简直就是光着下身儿走在这冰冻的世界里。比根儿大3岁的素桂戴的是一顶遮到她的眼眉的男式的旧火车头棉帽儿。这样的帽子在她的老家山东菏泽可以靠它过冬,而在这滴水成冰的松辽平原上,就几乎什么也不顶了!人们吐出来的唾沫,几乎在离开双唇的同时就凝结成冰块儿,落到地上时就跌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本能地侧着身子,尽量避开迎面刮来的凌厉的西北风,急匆匆地穿过离宋家屯镇只有一两里路的国家营子屯,继续朝正北的两家子屯挺进。
“赵大叔,唱一段儿吧?”道士背着风,揣着手,吃力地笑着提议。
人们用冻僵了的双手拍出并不响亮的掌声来表示附和道士的提议。
“好!你说唱,咱就唱!”赵凤山爽快地说道。“说吧,要听什么?”
“先唱河北梆子,再唱河南梆子!”道士说。
“小老妈儿在上房,自思自叹……”赵凤山唱起了河北梆子。
“哎!看哪!根儿,根儿!”素桂朝远处一指,惊叫起来。
众人一齐惊异地抬起头,见站在路旁一幢废弃了的瓜窝棚前面的果然是根儿!他穿着平时穿的那身棉袄棉裤,戴着上面只有栽绒的男式的旧火车头棉帽儿,穿着旧棉鞋,腰里系着一根麻绳儿,肚子鼓鼓的,不用说,那里面肯定是裹着装粮食用的面袋子。胡大珂看了根儿又气又恼又急又疼又为难。他明白,根儿是动了脑筋才想出这个主意的:他谎称找道士玩耍,一个人先偷偷地到半路上来等他们,逼迫胡大珂同意他去背粮。可是,天这么冷,他这么小,来回要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上百里的路,他怎么受得了呢!
“你奶奶和你娘知道你来了吗?”胡大珂没有申斥根儿。他很伤心,也很感动。孩子是因为不放心他才来的!是一片孝心!而且他的举动也表现了他的决心和心计。
根儿说;“俺对于清海家大婶儿说过了,让她告诉俺奶奶和俺娘。”
“真有心眼儿。”素桂说。
“好孩子,回去吧。”胡大珂温和地劝说道,“天太冷,路太远,你太小,来回上百里的路,你是连走都走不下来的呀,就更别说背粮食了。”
根儿冷静地说:“那你得和俺一起回去!俺明天就去趸烟卷卖挣钱养家。”
胡大珂耐心地说:“我和赵大叔说好了要去的,怎么好说了话不算数呢?”
“俺不管!”根儿固执地说。
“好孩子,听话,回去吧,你还小呀。”赵凤山说。
“俺不小!俺比素桂姐姐高!”
“俺比你大3岁!”素桂大声说道,“你还不到9岁呢!”
“俺是个男的!”根儿凑到素桂面前嚷道。
“半天一宿要在雪地里走一百几十里路,你怎么受得了呢?!”赵凤山摸着根儿冰凉的脸蛋儿说道。他喜欢根儿。根儿的孝心,聪明,勇气,都让他喜欢。
“俺不怕!”根儿不哭也不闹,就是不肯回去。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胡大珂有些气恼。
“爹,你就别去了吧,俺一天吃一顿饭就行,喝粥也中。”根儿说着哭了。
孙孝友听根儿这样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赵凤山无言地看着根儿。
“不行!你非回去不可!”胡大珂火了。
根儿不再说什么,一个人回身就朝北疾走。
“你站住!你爹和你一起回去!”赵凤山无可奈何。
胡大珂也有意和根儿一起回去。赵凤山说过,有次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在潘家油坊以北撞上警察。在月黑夜里,警察看不见他们,就放警犬追他们。距离越来越小,眼看就要追上了。赵凤山朝警犬扔去事先准备好的熟肉,可是警犬根本不理,还是穷追不舍。这时赵凤山抽出围在腰里的七节钢鞭,朝狗叫的方向猛力挥舞。警犬惨叫几声,就不再狂吠了。没有了警犬,警察就失去了追捕的方向,赵凤山才得以带领着他的穷哥们儿脱险。胡大珂想到上次赵凤山肯定打伤,或是打死了警犬,警察肯定会报复他们。这次背粮风险很大,带着根儿这样小的孩子,一旦遭遇警察,行动不便,容易落到警察手里。可是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也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儿听孩子摆布,只得无奈地说道:“那你就去吧。”
“到时候,俺背他!”赵凤山说。
“去吧,去吧,和俺做伴儿。”道士和素桂齐声说道。
在这冰冻的荒野里,这些衣衫褴褛的人,谁都没有一丝一缕的衣物可以拿出来接济别人,包括自己亲生的儿女。成年人对孩子们唯一能给的照顾,就是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身后,用自己的躯体构成一道透风的人墙,给孩子们挡一挡刺骨的寒风。在这生与死的交界线上,穷人对于儿女的爱只能有这样的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