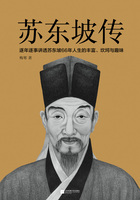
第2章 《初入仕途》:随父入京,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1056)春,眉山小城已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苏家庭院中,更是竹柏杂花,丛生满户。
那一天,苏轼早早就被母亲和两位新媳妇忙碌的脚步声惊醒。事实上,他也无法入眠。那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日子——苏家的三个男人,将要在这一天离开家乡,远赴京城——苏洵要带领两个儿子去参加当年的府试与翌年的殿试。
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
苏轼妻王弗、苏辙妻史氏,正帮着婆婆程夫人里里外外地忙活。她们恨不得把所有的爱意打包,让三个男人带着上路;又恨不得目光中能生出柔情的小手,牵住远行人的脚步。
眉山去京城的路,三个女人都不曾走过,但其艰险之状,早有耳闻。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行在那让飞鸟敛翅、猿猴悲啼的漫漫蜀道上,如何让人放心?
苏轼和苏辙并未看见母亲与妻子眼中的担心与离愁,在他们年轻的胸腔内,凌云壮志如迎风而起的帆,正急欲起航。
大踏步出门,头也不曾回。
褒斜谷曲折陡峭的古栈道,林深草密、荒无人烟的绵延秦岭,全然不在话下。一路走,还一路兴致勃勃地看山看水,游览沿途名胜古迹。
五六月间,苏家父子三人终于抵达京城。在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暂时寓居下来后,兄弟二人便投入紧张的备考中。
这年秋天,苏轼和苏辙一起参加开封府试,双双获选,苏轼更是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府试之后,还有礼部考试和殿试,兄弟二人丝毫不敢松懈。
苏洵原就对两个儿子充满信心,今初试身手便双双获胜,心里更加放松。他此次来京,一为带儿子求取功名,再者也希望以文章实现自己的入仕之梦。苏轼、苏辙在兴国寺的僧舍里埋头苦读时,老苏拣出早已誊好的几篇文章,拿着此前从张方平那里得到的一封举荐信,去往欧阳修的府上拜谒。
苏洵未曾想到,欧阳修竟对自己的文章大加赞赏,还将他举荐给了朝廷。如此还不尽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设私宴,欧阳修又特意将苏洵带上。
被一代文宗欧阳修如此不遗余力地荐举,朝中大佬们想不注意这个来自西南偏远之地的半大老头都不行。苏洵文名,先于两个儿子,鹊起京城。
欧阳修此时哪里会想到,“雏凤清于老凤声”,苏洵两个儿子的才华,日后更让举朝刮目相看。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知贡举,与王珪、梅挚、范镇等一同主持礼部考试。苏轼、苏辙再次同台竞技。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一鸣惊人。
这次考试的点检试卷官是梅尧臣。梅尧臣读过苏轼的文章后,认为此文引古论今,说理透辟,笔力稳健,语意敦厚,颇具大家的风采,欲取为第一名。他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读罢,大为赞赏,暗暗高兴,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师生之嫌,最后决定取为第二名。
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对这种只求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无一物的诗文,欧阳修深恶痛绝,遂与同仁们发起诗文革新运动,竭力提倡恢复古文。苏轼的文风,与欧阳修所提倡的可谓完全一致,加之苏轼本就才气纵横,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府试、省试顺利过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接下来是三月间的殿试。殿试中,苏氏兄弟依然畅行无阻,二人皆中。
嘉祐二年(1057)的京城,是“三苏”的世界。老苏的文章,大苏、小苏的功名,无不让人津津乐道。然而,命运何其残酷,那份成功的喜悦,还未来得及与远在家乡的亲人分享,便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病逝的消息。
程夫人是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算得名门闺秀。她嫁到家境清寒的苏家,应属下嫁。在嫁过来后的好多年里,她面对的都是不怎么上进的夫婿。苏洵老大不小了还在东游西逛,她心里虽着急,但嘴上从来不说什么,只低头默默做事,尽着一个妻子的本分。
苏家原本是中产之家,但因苏家几代人都乐善好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丁的不断增多,家财也散得差不多了。等到苏洵欲外出求官时,家里已无多少余财。可程夫人极富眼光,她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从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搬出来,到眉山城南纱縠行街租了一栋宅子,经营纱縠生意。此后,她全力支持苏洵外出游学,把家庭的重担全部揽到自己肩上。
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就读于天庆观北极院,师从张易简道士。后来,苏洵离家四处游历,苏轼便退学,由母亲教读。
如今苏氏兄弟刚崭露头角,母亲却永远离开了他们。
在接下来近三年的时间里,苏轼和苏辙皆在故乡,为母亲守制,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洵才再度携二子离蜀赴京。
这一次是举家搬迁,随行的不仅有苏轼、苏辙,还有两位年轻的媳妇。苏轼的第一个儿子苏迈即出生于这年赴京途中。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家一行人抵达汴京,在西冈租了一座宅院住了下来。
不久之后,朝廷授苏轼为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今河南渑池)主簿。因听说第二年要举行制科考试,兄弟俩均辞不赴任。
宋沿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得常才,又设制科以待非常杰出之才。参加制科考试的成员,须经大臣奏荐,先考于学士院,合格者才能参加御试,受天子亲自策问与拔擢。因为制科极严,应试者极少,得召者不过三分之一。当然,也正因为极严极难,考中制科者,其荣耀自是加倍于进士及第。
为了应付这场超级大考,苏氏兄弟必须全力以赴。他们从家中搬出来,住到怀远驿专心备考。举家寄身京城,吃穿用度自然紧张,兄弟俩在怀远驿的生活非常艰苦,每日三餐,都是白饭就着白萝卜和盐。但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他笑称此为“三白饭”。
时光飞逝,搬入怀远驿时尚是春天,转眼已是盛夏。考试的日子渐近,气温也如兄弟二人的紧张情绪一样节节攀升。苏轼想到兄弟二人不远万里,从蜀中赶到京城参加考试,如此辛苦,一旦考中,便要各奔西东,不知何时才能再过上这种无忧无虑相伴读书的快乐生活,于是在那个风雨之夜,他在怀远驿与弟弟苏辙做了一个约定:日后功成名就,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之后,一定要及时退隐林下,同归故乡,兄弟二人再如儿时一样,在故乡的山水间携手徜徉,对床夜话,共享天伦之乐。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制科考试。
按照规定,参加阁试者要在一天一夜内交出六篇文章,这对与试者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能够于文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本就不易,大多数参试者已无暇顾及文之工巧,而苏轼却在一天一夜间将深厚的学养、满腔的济世之志,付诸笔端,化成纵横捭阖、极论国是的文字,让司马光等秘阁考官叹为观止,视他为天才人物。
结果出来,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宋代的制科共分五等,一、二等形同虚设,自设立以来,无人问鼎。一般参试者,多以四等入选。苏轼之前,只有吴育一人曾入三等。
苏辙的对策文章也极受司马光推许,被定为三等。后来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覆考官认为苏辙在文中出言不逊,坚持不予。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闹到仁宗那里。仁宗道:“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虽然如此,苏辙最终还是被降一等,以四等录取。
那一天,对于苏家而言,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科考路上,父亲苏洵步步坎坷,频不得志,当时正奉命在京修礼书。两个儿子却在大考中一个三等、一个四等,占尽风光。
对于整个大宋朝廷来说,那一天也是可喜可贺的一天。据仁宗的皇后曹氏后来回忆,那天策试结束后,回到宫中的宋仁宗满脸喜色,对曹皇后说自己又得到了两位宰相之才。这二人便是苏轼、苏辙。
制策试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的官职;苏辙原以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但时为翰林院知制诰的王安石,对苏轼在文章中表现出的策士之风不满,又因苏辙的文章言辞尖锐,以为他将笔锋直对仁宗,从而不肯撰诰。
因苏洵当时奉命在京修礼书,苏辙便以父亲年老无人照顾为由,奏请留京侍奉。而苏轼则即将离开京城,前往凤翔,踏上他漫漫仕途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