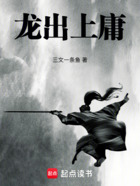
第45章 施以雷霆
上庸、西城、房陵,后世被称作东三郡,然而此时的三郡并未成型。
房陵原是汉中郡最为东边的边陲小县,地处筑水河流域,与荆州襄阳接壤。后来荆州刘表向四周扩张势力,安排了出身襄阳蒯氏的蒯祺攻取了房陵,并就地设郡,以蒯祺为太守,实际上一郡仅房陵一县而已。
上庸、西城两地,原先是由申耽、申仪兄弟在此间聚拢了数千家人口,且吸引了不少流民,人口较为稠密。其他地方虽也有人口聚集,但较为稀疏,主要集中在安阳、旬阳、钖县、平阳和武陵等县。
其中,安阳、西城、旬阳、钖县、平阳沿着汉水上下分布。安阳、西城所处之地,便是后世可媲美汉中的安康盆地。
上庸和武陵则在堵水河流域,武陵就是后世陶渊明著名的《桃花源记》中所提及的“晋太元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的武陵。
刘封盯着府衙中挂在案榻一侧的地图看得入神,周身气息仿若凝定,像是要将图中所绘的山川河流、关隘要塞,一股脑儿刻进脑海深处似的。
随着目光的深入探寻,刘封渐渐明白了为什么要设置东三郡的缘由了。原来这三处地方,分属不同的流域,各自被山川河流天然分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单独设郡,不仅能依据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施行更精准有效的治理,在军事防御上更是妙不可言。三处皆是进可攻,退可守,一旦有警,别处可互为犄角,相互策应。
历史上的刘备在攻取上庸之后,深知上庸、西城、房陵三地局势复杂,根基未稳。尤其是当地豪强申耽、申仪兄弟,在本地树茂根深,颇具势力,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刘备采取了安抚之策,任命申耽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又封申仪为建信将军,任西城太守。房陵倒是没有任命孟达为太守,而是让他领将军之号,驻扎房陵而已。
刘封复盘这段历史的时候,本就对刘备的安抚策略颇有微词,再听到众人纷纷介绍起申氏的种种暗中抗拒之举,他的内心更是充满了担忧与顾虑。
在他看来,申氏兄弟根基深厚且桀骜不驯,假如被赋予了军政大权,可谓如虎添翼。
长此以往,必然会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严峻态势,若是不加以敲打,日后必成大患。历史上的自己不就是被申仪背刺才丢失上庸,败逃成都的么?
而且时间紧迫,要是真想敲打申氏兄弟就必须要趁早。若等到刘备的教令下达,明确了众人太守、将军的身份,那时再动手,可就难如登天了。
一旦身份既定,各方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大乱。
如今趁自己奏报未送,刘备教令未下,局势尚还有些模糊,正是主动出击的好时机。他握紧了拳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暗自下定决心。
“诸位,请各位来,原先是准备商议如何给主公写请功奏报的,但从刚才各位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份报捷书还是暂缓发送的好。”刘封对着座下几人说道,随即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决定吐露给众人听。
袁秋、廖光等人围坐一堂,正堂中的气氛甚是凝重。
寇延率先发言,他站起身来,双手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依我之见,直接将申氏兄弟擒获,软禁或者逮捕,以绝后患,此乃擒贼先擒王之计!”
袁秋却缓缓摇头,目光望向众人,沉稳地说:“不可。申氏兄弟在这上庸经营多年,根基深厚,眼下他们手上的兵力不容小觑。若贸然行事,恐生变故。我觉得点到为止,稍加震慑,日后再以法度慢慢约束他们,才是稳妥之策。”
众人纷纷点头,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刘封一直静静地听着,此时,他微微皱眉,陷入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诸位所言皆有道理,我倒是有个想法……”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目光齐聚在刘封身上。刘封不紧不慢地说出自己的计划,众人听后,先是一愣,随后纷纷露出钦佩之色,赞叹不已。
上庸城中的牢狱阴暗又潮湿,墙壁上挂着几盏忽明忽暗的油灯,将整个房间照得阴森恐怖。
一向深居简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军正梁息面容冷峻,宛如一座冰山,端坐在审讯位上,而他的面前站立着的,正是旬阳降将申庆。
申庆本就胆小怯懦,在这阴森的环境下,被梁息冷酷的眼神一盯,吓得双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
梁息冷冷地开口:“申庆,你可知罪?”
申庆“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磕头:“军正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公子的事!”
梁息冷笑一声,一挥手,身旁的士兵捧出一堆黄金,在昏暗的灯光下,黄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梁息问道:“申庆,你是喜欢受刑,还是喜欢这些黄金?”
申庆看着黄金,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但又有些犹豫,结结巴巴地说:“大人,这……这是何意?”
梁息向前倾身,压低声音:“你只需如此这般……便可得到这些黄金,甚至还能更进一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申庆听后,心中一阵挣扎,最终,贪婪战胜了恐惧,他连连点头:“小人愿意,小人愿意!”
下午,阳光洒在上庸城的街道上,刘封在府中设下酒宴,邀请申耽、申仪兄弟。然而,热闹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申氏兄弟虽面带微笑,与刘封推杯换盏,但眼神中却透露出警惕。
刘封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满脸笑容地说:“两位将军,多亏二位保境安民,及时反正,归我主公,功绩卓著啊!此次我定会在捷报中为二位请首功,举荐申耽兄为上庸太守、征北将军;申仪兄为西城太守、建信将军!甚至再给你们请功封个侯都可以呢!”
申耽、申仪连忙起身,拱手致谢:“公子过奖了,我等不过是顺应天命罢了。公子用兵如神,胸怀广阔,现在又如此抬举我兄弟二人,我等钦佩感激不尽!”
骤然间听到刘封给出如此丰厚的许诺,任申耽、申仪心怀鬼胎,暗中提防,也不禁心旌摇荡起来。
酒宴正酣,突然,一名士兵匆匆闯入,在刘封耳边低语几句。刘封微微皱眉,随后对申氏兄弟说:“二位稍等,我去去就来。”申耽、申仪心中一惊,但又不好发作,只得在耳房等候。
原来,是申庆前来告发申仪私藏甲胄。申庆洋洋洒洒,一顿发挥,甚至连申仪平日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等种种丑事都抖落了出来。
刘封佯装不信,说道:“申庆,你可不要信口开河,这可不是小事!申氏兄弟真心归附于我,你莫不是挑拨离间么?”
在古代,历朝历代都将私藏甲胄视为重罪,汉代的周亚夫曾因在陪葬品中使用甲胄,就被下狱致死。
眼下虽是汉末乱世,朝廷的纲纪法度已然失去权威,各地的士族豪强们皆纷纷拥兵自重,有甲胄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假如刘封要上纲上线的话,就会授之以口实。
申庆连忙跪地:“公子,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啦,小人所言句句属实,起码申仪在私宅中私藏大量甲胄确有其事,公子若是不信,可差人一查便知。”刘封思索片刻,派申庆带着寇延前去查看。
耳房中的申耽、申仪顿时雷霆大发,要闯出耳房来与申庆对质,却被不知从哪闪出来的樊猛、寇真拦住。
樊猛冷冷地说:“请二位将军在此静静等候。”申氏兄弟无奈,只能在耳房内焦急地踱步。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又有人嚷嚷着要见刘封。
只见廖光押着一名府中小吏走了进来,廖光抱拳说道:“公子,此人为申仪办事,阴奉阳违,竟将军粮偷运至申家私仓,军中将士得知此事,群情激愤,要求严惩!”
刘封脸色一沉,看向小吏:“果有此事?”
小吏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跪下,哭喊道:“公子饶命啊!是申仪将军要求小人这么做的,小人不敢违抗啊!”
耳房内的申仪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差点摔倒。
申耽也看向申仪,一脸诧异,低声问道“这是真的么?”看来申仪的一些过分举动连申耽都被隐瞒而不知情呢。
此时,寇延带着申庆回来了。寇延单膝跪地:“公子,申仪私宅中确实藏有铁甲二十副,札甲两百余副,均未造册入库!”
刘封脸色阴沉得可怕,看向军正梁息:“军正,依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
梁息上前一步,冷冷地说:“私藏甲胄,不予入库,意图谋反,按律当处以申氏兄弟极刑!”
申庆突然“扑通”一声跪下,叩头说道:“公子,这都是申仪一人所为,与申耽将军无关啊!申耽将军忠厚老实,申仪奸诈诡谲,还望公子区别对待!”
刘封沉默片刻,遣散众人,然后来到耳房。申耽、申仪看到刘封进来,吓得连忙跪地。
刘封脸色严厉,大声斥责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私藏甲胄,偷运军粮,该当何罪?”
申耽俯身磕头:“请公子法外开恩,饶恕申仪之罪,饶恕我等之罪啊!”申仪则是瘫坐在地上,脸上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刘封扶起申耽,语气缓和地说道:“刚刚申庆说了,事情与你无关,何必如此呢。”然后拉着申耽的手看向申仪说:
“纵使你兄弟申仪罔顾国法,行径不端,但左将军一直谆谆教导于我,要常怀仁恕之心。念在你们举城投降,功劳卓著,我可以既往不咎。但申仪犯下大错,不得不有所惩戒。”
“此前所说的西城太守、建信将军之说不再作数,我会遣送申仪随同其他申氏族人入成都为人质,过后我还是会保举他任一方县长。他们即刻与我的请功奏报一同出发,一刻都不许耽误,由寇真护送上路。”
申耽听后,庆幸之余,连忙磕头谢恩:“多谢公子开恩,还望公子多多美言,莫要降罪于申仪!”
临近末了,申仪才似乎恢复了往日的桀骜与倔强,但此时也无力反抗,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刘封道:“今日我大意了,没想到着了你道。”
随后又转向申耽,心怀不甘地说:“兄长,此去一别,你多珍重,莫要让人给算计了。”
申耽无言,只能目送申仪的身影慢慢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