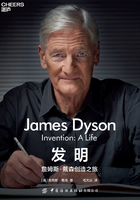
WHEN EVERYONE ELSE FEELS EXHAUSTED,
THAT IS THE
OPPORTUNITY TO
ACCELERATE,
WHATEVER THE PAIN, AND WIN THE RACE.
当别人都感到筋疲力尽时,
那就是加速的机会,
不管有多痛苦,
加速就能赢得比赛。
北诺福克沙滩上,一天中总有漫漫时光,大海、天空和沙滩交汇在一起,织成一个看似无垠的地平线。当清晨的潮水涌向沙滩,脚下的地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广阔的天空,你会觉得自己奔跑在一个看不见边界的空灵之地。
我所知道的自己第一件擅长的事就是长跑,这是我十几岁时自己学会的。一旦打破疼痛的屏障,我发现自己有决心,或者说有纯粹的冲劲儿一直跑下去。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跑步穿过那片令人难以忘怀的沙滩,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对于习惯的挑战,还是一种逃离学校的片刻愉悦,让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年少时,我的目标并不特别明确。当我18岁离开学校时,我的校长洛吉·布鲁斯·洛克哈特(Logie Bruce-Lockhart)写信给我母亲说:“我们很抱歉将与詹姆斯分别。我不相信他真的不聪明,我期待他会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尽管我们不得不假装学业很重要,但相对而言,它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不受那种无聊的、充斥着书本知识的学位束缚,你会做得更好。祝你在艺术学校有好运气。”当时,我很喜欢他在致我母亲的信中使用的双重否定措辞,也希望我的聪明才智“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但和他一样,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方面。后来回想起来,一位校长居然说生活不仅仅与学业有关,真令人耳目一新。
就洛吉个人来说,他绝对是人生赢家。他和蔼、有趣且机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他钟爱音乐、鸟类和水彩画。他曾5次入选苏格兰橄榄球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英国皇家骑兵团,曾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地驾驶装甲车驶进德国。他是我终生的朋友。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20年——他去世前不久。
我上的学校是格瑞萨姆学校(Gresham's School),位于诺福克郡的霍尔特集镇。这里风光旖旎但地处偏远,当时基本上没有汽车通行。我的父亲在此工作,担任古典文学主任。学校建立于“血腥玛丽”(1)统治时期,曾教育出许多极具个性的年轻人,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的颇负盛名,有的臭名远扬。其中有诗人W. H.奥登(W. H. Auden)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艺术家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和他的天才建筑师兄弟克里斯托弗·尼科尔森(Christopher Nicholson,1948年在一次滑翔事故中丧生),以及间谍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创建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里思勋爵(Lord Reith)也曾在这里就读。
除此之外,格瑞萨姆学校还培养出几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发明家:马丁·伍德爵士(Sir Martin Wood)发明了全超导磁体,从而促进了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产生,而磁共振成像仪是当今世界各医院和实验室的关键仪器;克里斯托弗·科克雷尔爵士(Sir Christopher Cockerell)发明了气垫船;再后来是航空工程师莱斯利·贝恩斯(Leslie Baynes),他发明了世界上功率最小的飞机——1935年问世的轻型卡登-贝恩斯辅机(Carden-Baynes Auxiliary)。
20世纪60年代初,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走上了与学术无关的道路。这并非因为我懒惰。恰恰相反,我全身心投入几乎所有非学术活动,关注各种各样的运动和音乐。我在9岁的时候学习演奏巴松,因为我之前从没听说过它,且它非常与众不同,也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然后,我也尝试了在戏剧中担任演员和舞台设计师。但我为我们的家庭剧、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的作品《批评家》所做的设计不太受欢迎。我是以类似“卷轴”的连续形式安排表演的,而非像“折叠纸”那样一幕一幕的形式,我认为这是在致敬18世纪晚期的戏剧时代。“你的节目太丢脸了,戴森,”我的舍监说,“你应该像展示纸张一样一幕幕将它呈现出来。”我的最后一部校园戏剧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我扮演的是特林鸠罗,而扮演睡在我旁边的卡列班的是蒂姆·尤尔特(Tim Ewart),他后来成了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节目《ITN十点新闻》的主播。
在学校里,艺术不是受重视的科目。我上第六学级(2)时,同桌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前英国皇家空军士官。他看出我对户外运动的热爱,建议我做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确实去见了剑桥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告诉我,我应该成为一名艺术家。我还去了圣乔治医院面试,当时它还没从海德公园角搬到现址图廷(Tooting),那里的人建议说我可能更乐意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
尽管当外科医生的想法对我有短暂的吸引力,但除了长跑之外,我最喜欢的是艺术。我想,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认真地画画了。我真正想做的是上艺术学校。自从遇到那位前英国皇家空军士官后,我就对接受或给出建议持谨慎态度。建议可能是善意的,但往往是错误的。鼓励是另一回事。我的观点是,如果建议和一个人的天赋相得益彰,那么这个建议可能是好的。这应该更像一种肯定。
然而,艺术并不是我的老师们为我设想的毕业后的职业或生活方式。考虑到我的父亲亚历克是一位古典文学大师,我的哥哥汤姆是剑桥大学的开放古典文学学者,我的姐姐莎妮在学术上同样出色,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从事学术研究。我擅长拉丁语,非常喜欢希腊和古代历史。不过,我是第三个孩子,和许多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一样,我从小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渴望,想通过走自己的路来证明自己。
我8岁到格瑞萨姆学校上学。从1946年起,我家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有过堂风穿过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冬天很冷。我父亲是剑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曾在肯尼亚教书,后在阿比西尼亚作战。1946年,他从驻扎在缅甸的比尔·斯利姆(Bill Slim)第14军北方兵团服役回来时,头发稀少,牙齿稀落。缅甸的战争非常艰难,派遣令中两次提到了父亲,他曾在英帕尔地区狙击手出没的丛林中经历过激烈的战斗。他还与印度、非洲、中国和美国军队,以及当地的掸族、钦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那加族民兵团并肩作战。英国军队,连同从欧洲以外许多地方抽调过来的同盟军,是在缅甸和那加山击败日军的大批参战者之中的一小部分。
我记得父亲是一个时刻快乐的博学者。他以少校的身份管理学校的学员队伍,教曲棍球和橄榄球,还教我在诺福克湖面上驾驶救生艇。他过去常常一大早叫醒我,只是为了赶上莫尔斯顿的大潮。就连1954年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暴雨肆虐北诺福克泥沼、湿地和山谷的情况下,他仍然这样做。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跳进车里、飞奔去找船的经历。我记得,我们的车是一辆过时的Standard 12,装载捷豹发动机,需要用手动曲柄启动发动机,启动时总发出剧烈的晃动声,而且频繁出故障。这的确是一次冒险。
我父亲在一个乐队里演奏次中音竖笛,还创作过校园戏剧——至今我仍能看到他标写在莎士比亚微缩版文集中的旁注。他很享受待在工作室里,用熔化的铅浇铸成各式各样的迷你士兵,或者做木工活。他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儿童书,书中用精美的水彩画作为插图。这本书的名字是《王子和魔毯》(The Prince and the Magic Carpet)。我很高兴,我的孙辈们非常喜欢我给他们读这本书,他们总是欢唱着“Dhurry Dhurry ooper jow”想象地毯飞舞起来。父亲还会即兴创作颇有寓意的打油诗。在他的讣告中,一位他的同事感慨,他们非常喜欢父亲的幽默,这种幽默颇有点拉伯雷式的夸张味道。此外,父亲还是一名业余摄影师,他自创了一种打印照片的方法,总是乐此不疲地将照片粘贴到珍贵的相册中。他总是在做一些让我们参与其中的事情,不管是喂鸡,让我们斜着身子靠站在汽车的踏脚板上,还是给格瑞萨姆学校的演员化妆。
当父亲遇到我的母亲玛丽时,她才17岁。母亲是剑桥郡偏远的福米尔地区牧师的女儿,也很有艺术天赋,她画了许多漂亮的水彩画。我的祖父是一位杰出的退休校长,他和我的祖母住在附近的思雷普洛小镇。我的父母在当地的一次社交活动中相识,并在1941年享受了一场短暂的战时蜜月。当然,我父亲当时还在军队中服役。母亲错过了上大学,之后上了一所剑桥的私立学校——佩斯学校(Perse School)。我不知道她的父母如何负担得起那里的学费。随后,母亲志愿加入了空军女子辅助部队(WAAF),服役于西萨塞克斯郡的坦米尔皇家空军(RAF Tangmere)。她曾驾驶着飞机飞越辽阔的欧洲版图。从不列颠之战开始,坦米尔成为重要的战略机场。它在战争电影中非常有名,其中一个经典的镜头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站在阳台上低头看地图。
我的姐姐亚历山德拉(莎妮)出生于1942年,哥哥汤姆出生于1944年,他们都是在战争时期出生的。我出生于1947年和平时期的诺福克,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没有足够的暖气,没有新玩具,几乎没有消费品。我们的钱只够勉强度日。那是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在我7岁前,一切生活用品还都是定量配给。我们自己种蔬菜,养鸡,收鸡蛋。有时,我们会步行去霍尔特的电影院看电影。不过,我们小时候仍有一些有趣的、值得珍藏的无价之宝:格瑞萨姆学校的操场、运动场、网球场和游泳池,整个假期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自由地玩。据说,格瑞萨姆学校的土地面积(英亩数)比学生数量还多。更不用说,辽阔空旷的诺福克沙滩就在学校旁边。
那座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有3户居民。我的玩伴都是格瑞萨姆学校老师的孩子。我们分成了好几个帮派,有“神气五人帮”“七人秘密行动队”“燕子号和亚马逊号”(3)。我是里面最小的,所以我总想要证明自己。我的身高也是我这一帮派以及课堂上最矮的。15岁的时候,我的身高突然猛长。孩提时,我们的所有活动就是围绕着格瑞萨姆学校跑来跑去,这在如今可能会被嘲笑,或者因为太危险而被禁止。我们挖过危险的隧道,攀爬过耸入云霄的大树,身上总是邋里邋遢的,还不时弄出点擦伤,满学校跑啊跑,总是气喘吁吁。我们挖隧道是协作完成的,每个伙伴挖自己的洞,然后用壕沟把洞连接起来。之后,我们把原木或废弃的木材放在壕沟上面,再用生锈的铁皮将它们围起来。这是一堂有趣的建筑课,没有人被活埋可真令人惊讶。那段日子就像田园诗一样!
1955年,我8岁的时候,我们开车从康沃尔郡波尔泽斯的一个海滩度假回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主要因为我当时屁股上长了个不舒服的疖子,导致我们不得不提前返回。我们停下来在达特穆尔野餐。我独自沿着一条小路走动,企图寻找一种长得很高的蕨菜。在一个拐角处,我发现父亲吐得很厉害。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说:“别告诉妈妈。”他不想引起恐慌,这是他的典型风格。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对他感到无比的怜惜和同情。
父亲于1956年去世,那时我9岁,他40岁。他服役回来时已经30岁了。3年后,他被诊断出喉咙处和肺部患有癌症。他在课堂上都是通过扩音器讲话。吉姆·威尔逊(Jim Wilson)曾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2016年出版的《格瑞萨姆旧事》(Old Greshamian Magazine)中回忆说:“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他靠着麦克风和扩音器坚持上课的勇气。但是当时,我们真的能欣赏到这种勇气和决心吗?”
他最后的日子是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医院度过的。我们从后门挥手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皮箱向我们告别。然后,他动身前往霍尔特车站,坐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幕时,他那勇敢的乐观总是令我哽咽。很难想象父亲挥手告别时的心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在去往伦敦的路上死去。更遗憾的是,他在缅甸打仗的那些年,一直与他年轻的新娘和家人分开着。
60多年来,这些记忆不曾褪去,我对于他错过享受3个孩子的成长以及美满婚姻的那种难过也不曾褪去。他应该很喜欢和他的孙辈一起玩耍吧!他要是能看到他的7个孙辈该多好!尤其当我看到我的外孙米克,长到我父亲去世时我的年龄时,我感到更加痛苦。米克很有爱心,聪明极了,做事沉稳镇定,不过仍喜欢带着他那只皱巴巴的、柔软的玩具小狗上床睡觉。他太稚嫩了,不能失去父亲。当我看着米克和他充满创造力与爱心的父亲伊恩一起打乒乓球时,我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父亲。
1956年的那天,我和哥哥汤姆、母亲在霍尔特家里喝芦笋汤时,电话铃响了。当母亲接电话时,我似乎预感到了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没有意识到癌症是一个避无可避的杀手!我们为我那才华横溢的姐姐莎妮感到忧心,她还在寄宿学校,她一个人是怎么接受这个消息的呢?
那时我刚到格瑞萨姆学校上学。几天后,我穿着短裤,膝盖骨向外鼓包着,在学校的小教堂里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家人坐在一起,而是和其他同龄男孩坐在一排。估计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拖到一个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的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很痛苦。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他们本不想无礼,但故去的人并不是他们的至亲。
父亲的离开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想起他的爱、他的幽默,还有他教给我的东西,以及未来没有他的日子,我充满了担心。尤其是寄宿在学校后,远离了家人,我经常突然感到孤单。在难过的时候,我不会流泪,也不会有明显的情绪起伏,只是紧绷着上唇。从那以后,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直在努力填补未能与父亲好好告别的空缺,并努力适应没有他陪伴的日子。也许我必须尽快学会为自己做决定,自力更生,接受冒险。没有什么比父亲的离开更让我感到糟糕的了。
慷慨大方的洛吉校长和他善良的妻子乔安排汤姆和我成为寄宿生,费用很低,这样我母亲就可以出去工作了。在受训成为一名教师之前,她靠给别人做衣服维持生计。后来,她又以大龄学生身份攻读剑桥大学的英语学位。父亲离世后,是母亲把我抚养长大,她对我孩童时期的学习影响很大。我的父母虽然结婚长达15年,但在父亲被诊断出癌症之前,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也就3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母亲能够在独自抚养3个孩子的同时还能读完两个高等教育学位。
母亲身高1.8米,身形高大,严于律己。不过对我来说,她总是温和而充满爱意的,甚至是宠溺的,尽管她没有什么钱。这些足够了。她的言行鼓励着我们。她如饥似渴地读书,与格瑞萨姆学校的学者们保持联系。尽管她之前从未去过法国,但她的法语却说得很流利。当终于有机会去法国时,她把我们带上她的Morris Minor旅行车。我们挤在一个廉价的三角帐篷里露营,她绘声绘色向我描述沙特尔大教堂的华丽扶壁、韦兹莱教堂的波形瓦屋顶,以及托罗内修道院内美丽朴素的西多会回廊。我们在法国多尔多涅河边搭起帐篷,并在河里游泳。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曾是英国属地。
我们下定决心,即使手头并不宽裕,也要努力好好过日子。在家里,我们在斯蒂福奇沼泽中采摘海蓬子,从沙子中挖鸟蛤。我们去看了本杰明·布里顿的首场歌剧演出,以及他亲自指挥的作品,他当时住在萨福尔克。我母亲会播放凯瑟琳·费里尔(4)和彼得·皮尔斯(5)的唱片。我们一起阅读,玩字谜游戏,并且制作一些东西。我喜欢剧院的铅制士兵、滑翔机和柴油飞机模型。我并没有玩士兵模型,也没收集它们。我喜欢的是制作它们。我用父亲的设备在坩埚中熔化铅,然后将危险的熔化后的铅倒入模具中。
1957年,当我母亲考虑职业时,她去诺里奇师范学院学习了两年的课程,想必是靠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她在朗顿山(Runton Hill)学校任职之前,在谢林汉姆现代中学(Sheringham Secondary Modern)教书。朗顿山学校是当地一所相当好的女子公立学校,它为她提供教职并让她担任一栋新寄宿楼的舍管。
1968年,在我离开家外出求学的3年后,我母亲决定在剑桥大学新学堂(New Hall)攻读学位。作为一个在战争时期步入婚姻的女性,她一定后悔没有完成中学教育,也没有机会像我父亲和哥哥一样上剑桥大学。即便这样,她也一定会为自己不得不又一次靠助学金过活,并居住在地下室而备感沮丧。我在伦敦时也住过地下室,因此能明白她的感受。尽管她因病住院,一直到考完期末考试,她依然拿到了二等一级的成绩。之后她到费克纳姆文法学校教英语,在那里度过了5年快乐的时光,并开始了戏剧创作。但命运弄人,1978年她被诊断出患有肝癌,并在不久后离世。
我妻子常说我继承了母亲的决心和勇士精神。母亲确实对我期望很高。她的胸襟也很宽广,能和不同年龄段的天主教徒成为朋友。她有领先于时代的思想,对各行各业的人都很宽容,也很乐意讨论任何事情。对于一个牧师的女儿来说,这似乎不同寻常。然而,也许她所持的任何关于等级尊卑的想法,都会因为战争带来的社会困苦和贫瘠而改变。
她引导我了解和认识更加广泛的文化,鼓励我尝试戏剧表演,演奏巴松,绘画,做所有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偶尔,她会来看我玩我喜欢的运动。也许,她本能地理解运动带给孩子的益处。她从不对我的学业成绩太过失望。她本人是一位热忱的业余艺术家,我父亲也是,她应该会暗自高兴她的一个孩子可能成为艺术家。后来,当我从事制造和设计时,她也对这些很感兴趣。
她和我的校长洛吉对教育持有相同的看法。虽然教文化课是主要目的,但学校还可以教授其他有教育意义的课程。我好好学习过,也乐在其中,但我对学业并没有多大的进取心。我把这股劲儿留给了体育运动和生活中可以发挥创造力的事。13岁时,我不得不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我选择了古典文学,并在15岁通过O级考试(6)后专攻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历史。然而,其他学科更吸引我。现在看来,我会很容易地说出我应该学习数学和科学。我喜欢这些,而且我数学很好。不过,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没有想到它们适合我。在这件事上,我令我的老师们很沮丧,他们也对我很失望。我不主张孩子们以我的选择和玩世不恭的学习态度为榜样。后来,我确实爱上了学习。我在艺术学校和皇家艺术学院刻苦学习,钻研进取。现在,我热衷于阅读历史书,而数学、工程学和写作已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游戏中,我明白了刻苦练习、团队合作和战术的重要性。出其不意的战术规划,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生课程。这些能力不太可能从文化课中学到,当然也不可能从死记硬背中得到。戏剧表演,这种我非常喜欢的活动,教会了我读懂人性,表达思想,掌握讲话的艺术。长跑,不仅让我自在徜徉于诺福克的荒野美景中,也让我明白我只能依靠自己。跑步还教会了我打破痛苦的屏障:当别人都感到筋疲力尽时,那就是加速的机会,不管有多痛苦,加速就能赢得比赛。克服研究中看似不可能的困难和生活中的其他挑战,需要毅力、决心和创造力。
学校不教创造力,这一点让我觉得悲哀和担忧。然而,眼下世界对创造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需要为看似棘手的问题创造新的解决方案,设计新的软件,创造不同的东西,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如今,这种能力是先决条件。我们再也不能通过重复我们已学到的,复制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过日子了。谢天谢地,这个世界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竞争也空前激烈。西方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优势正在减弱。为了保持领先,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创造力。
在戴森,我们一直致力于追求我们所说的“精益工程”(lean engineering)。值得高兴的是,当今业界对可持续资源一致认同,即资源投入越来越少,性能越来越好。不过,要实现这种突破,所需的团队日趋庞大。拿工程来说,30年前,我们只需机械工程师。现在我们需要电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和人工智能科学家……队伍还在壮大。
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一体化。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开发技术并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意味着,除了培养出最优秀的工程师或科学家,我们还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应用我们开发的最新技术。不然,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将会抢占鳌头。
家庭生活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从8岁起,我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学会了分担家务。20世纪50年代,在我们租下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里,没有打理园艺和耕种的机器。我们有一台适用于大花园的推式割草机,以及一把可以挖菜的铲子。我们的“洗衣机”是一个废弃的锅炉,它只能用于浸泡衣服,浸泡后我们再在水槽里漂洗,最后在一个难用的轧水机中脱水。我们唯一的电器是一台旧直立式吸尘器,它的把手上挂着一个布袋。我们家里的墙上没有电源插座,所以打扫每间房屋的时候,都要站在凳子上,把吸尘器插头插到中央照明插座上,还得注意不能使劲拉扯吸尘器的电线。这台吸尘器又臭又脏又没用,困扰了我很多年!
我由衷地感谢母亲让我参与了这些家务活。她教会我缝纫、编织、制作地毯以及做饭。父亲教会我远航。我喜欢看他做木工活。我自学了制作飞机模型,给它们装上发动机,让它们飞起来,也自学了修理自行车。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东西、自学成才、无所畏惧,这些成了我的第二天性。通过制造东西来学习和通过课本知识学习一样重要。真切的体验是强大的老师。也许我们应该多注意这种学习方式。并非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学习。
我想我是一个喜欢自学的人。通过经历失败,我会找到自己的方法把事做成。我把这一点归结为8岁以后没有父亲告诉我该如何做事情。但我注意到,我的两个儿子也有同样的特点。我还没来得及向杰克演示如何使用车床,就亲眼看见他自己让车床运转起来。萨姆则是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而埃米莉不同,她要去上滑雪课才能滑得熟练,杰克、萨姆和我都是自己学会滑雪的。我们通过亲自尝试获得经验,来理解并确信自己是以正确的方式在做事的。通过尝试和犯错,或者实验来学习,这种过程很让人兴奋,所学到的经验教训也是根深蒂固的。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从失败中学习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应该欢迎失败,而不是避免失败。工程师、科学家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害怕它。
不过,我确实很想念我父亲。许多年后,我在弗吉尼娅·艾恩赛德(Virginia Ironside)所著的一本书中了解到,85%的英国首相——从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到约翰·梅杰(John Major),以及12位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贝拉克·奥巴马,都在童年时失去了父亲。如果说早年丧父是通往成功的某种可怕的门票,那就错了。但也许,年少的缺憾有时能激励人们取得巨大成就?
即便如此,我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的冒险经历,与我那些聪明得多的哥哥姐姐的经历还是截然不同的。我哥哥当了老师,我姐姐做了护士。我的心魔驱使着我走更远的路。小时候,我对亚瑟·兰塞姆的《燕子号和亚马逊号》一书中沃克夫人收到的来自丈夫的电报很感兴趣。孩子们请求驾着燕子号小船前往梦寐以求的湖中荒岛独自露营,那位远航的海军军官是这样回应的:“被淹死总比做个笨蛋强,如果你们不是笨蛋,那你们就不会被淹死。”我不想成为一个笨蛋。
父亲去世后,每逢学校假期,我继续和伙伴们过着《燕子号和亚马逊号》中的生活。我帮忙做家务,用轻木制作飞机模型,有些飞机还装有小型柴油发动机。我开始在学校寄宿了,只在假期才回家。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半学期,虽然我家离学校很近,但在我心里,家似乎很远。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男孩子是不允许表露感情的。当遇到不公正对待,受到欺凌,或被人同情时,我都会抑制自己内心翻涌的情绪。那里的老师,和当时其他地方的老师一样,可能会残酷地挖苦学生,对于学生的情感需求毫无意识。一连14个星期,没有人能离开学校,也没有父母前来安慰或告诉我们不要担忧。我太期望放假了。
无论学校生活怎样起起落落,我都意识到周围的天地更加广阔。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可不容小觑。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成为首位4分钟内跑完1英里(7)的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并插上了英国国旗。彼得·特威斯(Peter Twiss)驾驶超音速飞机费尔雷“德尔塔”2号,成为世界上首位以超过每小时1 000英里速度飞行的人。捷豹D型车连续3次赢得勒芒24小时耐力赛冠军。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共同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社会失业率降低,紧缩时代阴霾消散,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宣称:“人民的生活从未如此好过。”与此同时,大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我们学校地图册上四分之一的区域都属于英联邦版图。
每周,一本发行量巨大、插图精致的男孩漫画《鹰》(Eagle)会刊登技术插图师莱斯利·阿什韦尔·伍德(Leslie Ashwell Wood)的作品,他很擅长绘制由中心展开的彩色剖面图。他画了一些新型喷气式飞机、涡轮机车或核电站,以及英国工厂、车间和实验室里出现的各种发明。现在,很多工厂、车间和实验室早已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沉闷的新住宅区或便利超市。有趣的是,我9岁的时候,凭借一幅诺福克海景油画《布莱克尼一角》赢得了1957年的《鹰》绘画比赛。那是父亲去世后不久,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安抚了我受伤的幼小心灵。我的绘画水平得到了认可。我后来了解到,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杰拉德·斯卡夫(Gerald Scarfe)都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过——就在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那里之前,他们的处女作都是在《鹰》中亮相的。《鹰》带我走进了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力的世界,让我一边享受惊心动魄的海陆空冒险,一边与艺术和工程不期而遇。
作为男生,我们深信英国人是最优秀的。毕竟,我们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德国和日本。很显然,即使我们没钱添置新衣服,买不起洗衣机和冰箱,只能从破旧的燃煤炉子获得少得可怜的热水,我们也有能力在和平时期创造新纪录和新发明,赢得胜利。
我们对本土汽车也很支持,我家就有两辆最好的:Morris Minor旅行车和Mini汽车。它们都是由我崇拜的工程师亚历克·伊西戈尼斯(Alec Issigonis)设计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敢肯定,它们在转向、抓地力、悬架和全方位视野方面都比大众甲壳虫优越,而大众甲壳虫是它们当时唯一真正的外国竞争对手。为了向传统致敬,我们的两辆车都装饰了木条,尽管它们采用了现代工艺,但它们仿佛都是带轮子的微型农舍。
我们曾经把13个男生塞进了母亲的Morris Minor旅行车。这一定创下某种纪录了。我知道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车很有趣,但“设计”这个词在当时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辆车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在半个世纪前的北诺福克,乃至英国的任何地方,却一点也不,甚至可以说是漂亮。尽管在那些日子里,北诺福克相当贫穷,但对我来说,它仍然是世界上遥远又迷人的一角。
在学校里,我虽然学习不够努力,但过得还不错。我通过了艺术、数学、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英国文学和历史O级水平考试,相当于获得了今天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并且艺术、古代历史和通识学都通过了A级水平考试。在假期,我尝试了当地各种类型的工作,把一袋袋又冷又湿的土豆装上卡车;处理冰冷的芽甘蓝菜,将不可食用的部分摘掉;以每桶10便士的价格采摘黑加仑子;采摘欧芹并运输到当时位于金斯林的超现代化的金宝汤工厂,这是大西洋一带最大的汤品加工厂。
学校的日子也越来越让人兴奋了,我们和朗顿山学校六年级的女生一起在格瑞萨姆学校上课。朗顿山学校是我母亲曾经教书的学校。那些女孩们非常有学术抱负。我那时的女朋友卡罗琳·里卡比(Caroline Rickaby)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剑桥大学,后来又攻读了杜伦大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约翰国王与其法国顾问的关系。通过她,我才知晓,这个英国国王受到了多大的歪曲。我对历史一直有兴趣,但我的天赋不在这里,而是在其他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