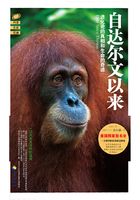
5 等级问题
在《亚历山大的宴席》(Alexander's Feast)中,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①描述了他的英雄在酒足饭饱之余,重述他的那些业绩辉煌的故事:
国王自得难按;
将打过的战役又打了一番;
再一次击溃了所有的敌人,
将已经杀掉的又杀了一遍。
150年以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与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就海马回的争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愿乘胜追击,他援引了同样的想象:“我们的生命太短了,不能将已经杀掉的再杀一遍。”
欧文通过提出人脑中有一种小的回转部(海马回),在黑猩猩和大猩猩(及其他所有生物)中则没有,只存在于智人(Hoao Smpiens)中,而确立我们的独特性。但已经解剖过灵长类的赫胥黎——当时正准备他的著作《人在自然中位置的依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则明确表示,所有的猿都有海马回,而且灵长类脑的不连续性只存在于猿猴(狐猴和眼镜猴)与其他灵长类(包括人类)之间,而不存在人与猿之间。在1861年4月这一个月里,整个英国都在关注她的两位最伟大的解剖学家关于脑中一个小小突起的无休无止的争论。《笨拙》(Punch)周刊嘲笑地用韵文记述了这个事件,而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①在1863年出版的少儿经典读物《水孩儿》(The Water Babies)中详细写了“海马回”。他提到,假如找到了小水孩儿,“他们会赋予他灵气,或登在《新闻画报》(Illustrated News)上,或者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切成两半,一半送给欧文教授,一半送给赫胥黎,看他们如何谈论”。
那时西方社会已经容纳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含义。海马回的争论却是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调和中的最大障碍,即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与自然之间存在连续性,我们热衷于寻找证明我们人类独特性的标准。伟大的博物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阐明一般的自然理论,却将人类视作唯一的例外。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认为世界是静态的(见文章18),生命的复杂性不随时间而变化,所有生物的结构与功能从一开始就保持不变;人类是地质时期中瞬间创造出来的,在其解剖结构与功能恒定的基础上,精神的特征一跃而现。而阿尔弗莱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作为一名热情的选择论者,在坚决地坚持自然选择是进化变化中唯一指导力量方面,比达尔文还达尔文,也认为在解释人脑方面是个例外(后来他转向唯灵论)。
而达尔文虽然接受了严格的连续性观点,却不愿意表达他的异端。在《物种起源》(Oringin of Species)第一版(1859)中,他写道:“有关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将会阐明。”后来的版本中加上了强调句“更加”。只是到了1871年,他才有勇气出版《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见文章1)。
长期以来黑猩猩和大猩猩一直是我们探讨人类独特性时争论的问题。因为假如我们在种类上而不是程度上区分我们人类与我们的近亲,我们便为长期探讨我们在宇宙中的自大找到了理由。这场争论很久以前就不再是简单的关于进化的争论,有教养的人现在已经接受了人与猿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观点。但是我们与我们的哲学和宗教遗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仍在寻找我们与黑猩猩之间在能力上的严格区别。正如赞美诗中所唱:“什么是人,人有心灵,人仅次于天使,人充满光荣和荣誉感。”人们尝试过许多标准,而这些标准一个接一个地失效了。唯一诚实的选择是承认我们与黑猩猩之间在种类上是连续的。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只是古老的灵魂概念变得更加微不足道,而且还弘扬了我们与自然统一的观点。我提出三个标准,从而比起其他的观点,甚至比起赫胥黎大胆的设想,更加认为人类与黑猩猩关系很近。
1.欧文传统的形态独特性。赫胥黎永远熄灭了那些寻找人与猿之间解剖上不连续的热情。然而,在某些方面,这种寻找还在继续。成体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无论各部分,还是器官的位置,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相对的体积和生长的速率上,我们存在着差别。D.斯塔克(Prof.D.Starck)教授及其同事本着德国解剖学研究重视细节的特点,最近研究得出结论,人与黑猩猩的颅骨之间仅有量上的差别。
2.概念上的独特性。自从欧文溃败之后,没有哪个科学家再坚持推出解剖学的依据了。相反,人类独特性的捍卫者则坚持认为人与黑猩猩之间在心智能力方面存在不可逾越的隔阂,为了证明这种隔阂,他们一直在寻找明确的区分标准。早一代的人援引使用工具,但是聪明的黑猩猩可以使用各种人工制品去获取难以得到的香蕉,或释放被囚禁的同伴。
最近的观点则集中在语言和概念化上,这是种类上潜在差别的最后堡垒。早期教授黑猩猩谈话的实验显然不成功,仅仅使黑猩猩产生出轻微的喉声和微弱的发音。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失败反映了中枢构造上的缺陷。但这种解释显得太简单了,很不深刻(当然如何说明在自然条件下黑猩猩的语言能力还是次要的问题):黑猩猩的声带构造使它不能发出连续清晰的声音。如果我们能找到另外的途径与黑猩猩交流,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远比我们设想的要聪明。
但是现在所有的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已知道另一种方法产生出的惊人成果,利用聋哑人的手语与黑猩猩进行交流。当耶基斯实验室(Yerkes Laboratary)的明星学生拉娜 (Lana)开始询问它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的名称时,我们还能否认黑猩猩也具备概念化和抽象的能力吗?这不只是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1975年2月,R.A.加德纳和B.J.加德纳(R.A.Gardner and B.T.Gardner)报道了他们利用手语训练刚出生的小黑猩猩的结果。(哇!他们以前的研究对象是一岁后才开始进行手语训练的,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它的词汇中仅有两个信号)三个月之后,两只黑猩猩都开始做出可识别的信号。其中一只黑猩猩莫雅(Moja)在13个月后,已经会了四个词:来给我,走,多,喝。它们现在的进步并不比人类中的孩子慢(我们通常只是等待孩子的讲话,并不了解孩子在讲话之前向我们做出的信号)。当然,我并不相信我们与黑猩猩之间在心智上的差别仅仅是抚养的问题。我并不怀疑与人类的孩子获得的成就相比,这些幼小黑猩猩的进步相对会慢下来。我国下一任总统不会是另一个物种。然而,加德纳家人的工作还是令人惊奇地证明了我们是如何低估了我们在生物学上最近的亲戚。
3.遗传学上的整体差异。即使我们承认从单一特征和能力上无法完全区分人类与黑猩猩,至少我们能够证明我们与黑猩猩之间有很大的遗传的整体差异。总之,这两个物种外形区别很大,而且在自然条件下做不同的事情。(虽然实验室里的黑猩猩表现出了准语言能力,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在野外具有丰富的概念交流)但是,最近玛丽-克莱恩·金(Mary-Claire King)和A.C.威尔逊(A.C.Wilson)发表了关于这两个物种遗传差异的观点(《科学》, Science,1975年4月11日),而且我想这个结果将推翻多数人仍然坚持的一种先验性的偏见。简单地说,他们利用所有的生化技术,尽可能多地检测蛋白质,发现这两个物种遗传上的整体差异很小。
两个物种形态差异很小,功能上分离,而且在自然中是生殖隔离的群体,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兄弟种”。比起属于同一属但形态差别明显的物种(同属种),兄弟种的遗传差异要小得多。而黑猩猩与人类显然不是兄弟种,就是按照通常的分类实践,我们甚至也不是同属种(黑猩猩属于黑猩猩属,Pan,我们属于智人属,Homo sapiens)。然而,金和威尔逊已经表明,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遗传整体差距比兄弟种之间的平均差距小,比测试过的任何同属种之间的差距更小。
一个出色的悖论。虽然我执着地认为我们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但我们仍然是不同的动物。假如遗传整体差距非常小,这种差距在形态上和行为上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按照原子论的观点,生物的每一个特性是由一个基因控制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解剖上的不相似与金和威尔逊的发现协调起来,因为形态和功能上的差异是基因上许多差异的反映。
答案肯定是一些种类的基因效应更大,这类基因必定影响整个生物,而不仅仅是单个特性。即使遗传整体差异不大,这些关键基因的少量变化也可能使两个物种发生很大的差异。所以,金和威尔逊试图通过将我们与黑猩猩之间的差异归因于调节系统的突变,来解决这个悖论。
肝细胞和脑细胞都由同一染色体的同一基因控制,它们的根本差异并非是由于基因构成,而是发育的不同途径。在发育中,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时间开启和关闭,这样,即使是同一遗传系统,也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事实上,胚胎发育的奇妙过程必定是通过基因活动精巧的定时来调节的。例如,导致来自同源肢芽的手的差异性,必定是细胞突然在某些区域生长迅速(形成手指),而在某些区域则死亡(手指之间)。
许多遗传系统肯定专门负责确立发育事件的定时,即负责基因的开启和关闭,而不负责决定特定的特性。我们将控制发育事件定时的基因视作调节系统。显然,每一调节基因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生物造成巨大的影响。延迟或加速胚胎发育的某一关键事件,整个发育过程都会随之改变。金和威尔逊因此认为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主要遗传差异,在于最重的调节系统存在差异。
这是合理的(甚至必然的)假说。但是我们了解这种调节差异的性质吗?我们现在都不能确定其中所含的特定基因是什么,这样,金和威尔逊等于什么也没说。他们写道:“对今后人类进化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去证明黑猩猩与人类发育中基因表达定时上的差异。”但是我相信我们会了解这种定时变化的基础。正如我在文章7中提出的,智人种基本上是一种幼态持续的物种,我们通过放慢发育速度而由类猿祖先进化而来。我们会发现导致我们比所有灵长类相同的个体发育趋势放慢及使我们保持幼体生长趋势和比例的调节变化。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遗传差距很小这一点,可能会诱使我们去设想最具潜在兴趣但道德上却难以接受的科学实验:杂交我们两个物种,以探讨其后代像什么,至少部分是个黑猩猩。这种杂交极有可能,因为我们之间的遗传差距太小了。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一种完全可以和猿的行星上的英雄(指我们人类)相比的种族,我需要补充说明,这样杂交的后代应该是完全不育的,就像出于同样理由培育出的骡子一样。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遗传差异很小,但其中至少包括十个大的倒位和移位。倒位是染色体片段的扭转。每一个杂交细胞中将有一组黑猩猩的染色体和一组人类的染色体。卵和精子通过所谓减数分裂或还原分裂产生。细胞分裂之前,每一个染色体必须与其对应的染色体配对(相聚在一起)。这样,相对的基因相互配对。每一个黑猩猩的染色体必须与人类的相应染色体配对。但是,假如与黑猩猩相应染色体配对的人类染色体上的片段倒位了,那么没有染色体片段精致的回转和扭曲,基因对应的配对便不能发生,而染色体片段的回转与扭曲又会妨碍细胞的成功分裂。
这种实验很有诱惑力,但是我相信将一直严禁从事这种配对的实验。而且,我们一旦发现如何与我们最近的亲戚交谈,这种实验的诱惑无论如何也会减小。我想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黑猩猩了解到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① 德莱顿(1631—1700),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诗人。——译注
① 金斯利(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作家,支持达尔文学说,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水孩儿》是他的著名儿童作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