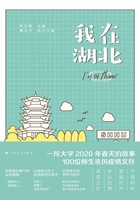
疫情之下食之变化
和往年一样,在春节来临前的腊月二十回到老家,我们一家三口、哥嫂二人以及小叔家的四人,一共九个人聚在了一起,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当时还没听到疫情的消息,加之年货备得充足,顿顿都能吃上肉,也不知精打细算、合理调配,但到了2月,因疫情封路,原本打算只逗留几天的我们只能继续留在老家,对95后的我而言,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馒头
春寒料峭的2月。
一天傍晚,晚饭要开始准备了。母亲让我去镇上买一些馒头。平时我们一家三口吃饭,三个馒头足矣。而现在九个人一起吃饭,一大袋子的馒头只够吃一顿。母亲给我十元钱,让我多买些回来。
来到镇上的超市,今天很幸运,刚好赶上老板新进了一批馒头。五元钱一袋,一袋十个。我决定买两袋,这样可以吃两顿了。
“来两袋。”我掏出十元钱。
“你只能买一袋。”老板态度很坚决。
这果断的拒绝让我愣了好一会儿。在当今这个社会,好像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来,怎么今天买个馒头还受阻了呢?拒绝我的是镇上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年纪不大,看着挺爽快利落。
“为什么啊?”刚从冲击中稍稍缓过来的我不禁追问。
“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啦,什么时候是个头都不知道,粮食也开始紧张,进点馒头不容易,得让大家都有得吃啊!”老板一脸严肃地说完,语气稍稍缓和,又补充道:“想多买明天再来吧。”
“行,谢谢哈。”我接过只够吃一顿的馒头回家,边走边琢磨着刚才老板的话,想着优秀的商人就应当这样。
分餐
馒头买回家,母亲已经在准备晚饭了。
她洗了一大盆菜,切了一小碗肉,淘了一大锅米,又将九个碗高高地叠起,拿出了一大把筷子。准备妥当,每人端一个碗,拿好自己的筷子,轮流走到菜锅前,先盛上一大勺菜,再拿个馒头,走出厨房,在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开始吃饭。
起初,我很不能适应这样的吃饭模式。过去三口之家,不管是菜还是饭,准备的量不多。每个人两个碗,一个盛菜,一个盛饭,菜端到桌上,大家一起边吃边聊,有滋有味。
但现在,九人同食,碗不够用,只能先把菜吃完,再去盛饭。本来宽绰的桌子显得狭小,坐得远了,还够不着菜,所以只能各盛各的,端着碗筷随便找地儿吃。凳子不够坐,只能坐沙发、坐门槛,散开去。以前我总觉得在一起吃饭图的是热闹,天南海北地侃一侃,一顿饭得吃个一小时,现在座位分散得开,疫情严峻,大家都少有谈天说地的兴致,吃饭不再是享受,倒像是完成任务。
梨汤
晚饭过后,母亲开始准备梨汤,这是进入疫情以来每日必备的饮品。大约从1月底开始,许是老人们都相信梨能润肺,许是受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公众预防指南之启发,整个村子,每家每户,每天必熬上一大锅梨子水,不论老幼,必须喝上几碗,以预防肺炎。
每逢去超市补粮,免不了买上一大袋梨子,而且不能一个人抱着一个直接啃,为了大伙都能成功地抵御病毒入侵,得紧着吃,要煮成梨汤。母亲会切上两三个梨子,再加上几颗冰糖,熬煮一锅又一锅,基本上能够一大家子喝两顿。在物资不充裕且采购不太便捷的疫情期间,每日都能喝上滚烫的梨汤也给了我们不少心理上的慰藉。
我家里小孩多,总有不听话的,偷偷地摸来一个梨子或一块冰糖就直接吃了。大人若是批评了显得小气,怕旁人笑话小孩儿连过年也不能吃得自在。可不是嘛,疫情之下,物资紧缺,运输不便,有时是买也买不着的。于是,大人们想尽办法把紧俏的东西藏起来,好像全家玩起了“藏宝游戏”。
还有些情况,也让大人为难。梨子煮成茶,即使加了糖,小孩也不那么爱喝。最初两天出于好奇,孩子们都会乖乖喝下,一连喝上几天后便厌倦了这个味道,有时大人盛了一碗让放凉了喝下,结果等凉透了还是没人来喝。大人只好一一点名叫来孩子们,像点卯似的,喝完一碗才能放任他们继续玩耍。
结语
疫情期间,我身处偏远的农村,离城市很远,所幸身边没有确诊病例,因此我不曾有那些太过焦灼的情绪,对疫情最深的体会来自这些细微的生活点滴留下的记忆。买不来的馒头,拥挤的餐桌,寡淡的梨汤,一家九口的生活,构成了我对这次疫情特别的私人回忆。
张倩 1997年生,湖北襄阳,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