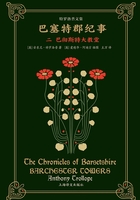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2章 根据议会法令改组后的海拉姆养老院
我在这儿长篇大论地向公众叙说一下这篇故事开始之前哈定先生的全部历史,这是没多大必要的。《朱庇特》上就他作为巴彻斯特市海拉姆养老院院长所支取的收入,曾经对他进行过攻击。公众不会忘了那位敏感怕事的先生是多么经受不起那次攻击的。他们也还不会忘了,约翰·波尔德先生曾经为那个慈善事业向他提出了控诉[21]。波尔德先生后来就娶了哈定先生身边当时唯一还没结婚的小女儿。哈定先生在那些攻击的压力下,辞去了院长的职务,虽然他的朋友和律师都极力劝他不要那么做。然而,他还是辞去了,并且勇敢地担负起了城内圣喀思伯特[22]那个小教区里的职务。他是那个教区的牧师,同时继续做着大教堂圣诗班领唱人的工作。这一工作报酬很低,以往一向被认为是上面所说的养老院院长理所当然的兼职。
他被人家那么无情无义地撵出了养老院。当他离开养老院,以自己谦虚朴实的方式在巴彻斯特大街上住定下来时,他并没有料到人家会不顾他的本意,进一步来充分利用这件事。他所希望的只是:这一行动也许做得很及时,可以防止《朱庇特》上再刊登出什么短评来。可是人家却不容他的事情就这样悄悄地平息下去。他们很喜欢谈论他所作的大公无私的牺牲,就和他们先前喜欢责备他的贪婪一样。
这时发生的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收到坎特伯雷大主教[23]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在信中,大主教热情地赞扬了他的行为,并且请他谈谈他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哈定先生回信说,他就打算在巴彻斯特当圣喀思伯特的教区长,这样这件事就搁下了。接下去,各家报纸(其中也有《朱庇特》)全拣起了这件事,用颂扬的口气把哈定先生的姓名传遍了国内所有的阅览室。大伙儿还发现,他就是那部了不起的音乐著作《哈定圣乐》的作者,——而且还谈到一个新版本,虽然我相信它始终没有刊印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部作品被圣詹姆斯宫的皇家小教堂[24]采用了,有一篇很长的评论文章出现在《音乐观察者》上,说以前的这类作品中,没有一部曾经把那么细致的研究工作和那么高超的音乐才能结合到一起,还断言从此以后,凡是培养艺术或重视宗教的地方,都会知道哈定的姓名。
这是很大的赞扬。我并不否认,哈定先生听到这些恭维话后,觉得很高兴,因为要说哈定先生对什么学科十分自负,那就是对音乐。可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第二版要是刊印出来,也从来没有人买,送进皇家小教堂的那几本又全不见了,它们跟一大堆类似的作品一起安安静静地搁在一边。《朱庇特》的托尔斯先生和他的同行们又忙着去议论其他人士,答应给予我们朋友的不朽名誉,显然是打算到身后再兑现的。
哈定先生跟他的朋友主教一块儿消磨了不少时间,跟他女儿波尔德太太——哎呀,她现在是一位寡妇了——一块儿也消磨了不少时间,而且几乎天天去看望留下的那几个他早先照管的可怜人,也就是海拉姆养老院这时候剩下没死的那几个受施人。他们这会儿只有六个人还活着。根据老海拉姆的遗嘱,人数应当永远是十二名。可是在院长离开以后,主教没有委派一个继任人,也没有指派一些新的受惠者进入这个慈善机关。看来除非当权的人采取某种步骤,使巴彻斯特养老院再一次发挥作用,否则它便会停办了。
过去五年里[25],当权的人并没有忽略巴彻斯特养老院,各式各样的政治“大夫”都曾经来处理过这个问题,哈定先生辞职后不久,《朱庇特》上就曾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应该怎么办。在大约半栏的篇幅中,它分派了收入,重建了房屋,结束了种种争吵,恢复了亲切友好的感情,为哈定先生作出了安排,并且把整个儿事情安顿在一种必然会使巴彻斯特市和巴彻斯特主教,以及全国各地都深感满意的基础上。这一方案的明智之处,从“常识”“真理”和“一个光明磊落的读者”等等写给《朱庇特》的那许许多多信中就证明出来了。这些信全表示出了钦佩,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所举的一些细节。说来也真奇怪,压根儿没有刊登过一封表示反对的信,因此,当然是没有人写过了。
但是人家并不相信卡桑德拉[26]。就连《朱庇特》的明智的语言人家往往也不愿听。虽然其他的计划并没有出现在《朱庇特》上,教会慈善事业的改革家们却并不放慢脚步,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宣布了他们各自使海拉姆养老院再度发挥作用的秘方。一位博学的主教抓住机会在上议院里提到了这件事,并且表示他已经就这个问题跟巴彻斯特主教通过信了。斯泰利布里奇[27]的那位激进的议员提议,把这笔款项改去充作乡下贫苦农民的教育经费。他提到一些关于所讲的农民的迷信与习惯的轶事,使上议院感到很有意思。一个政治小册子的作者写了好几十页,管它们叫作《谁是约翰·海拉姆的继承人?》,想对所有这类机构的管理订下一条绝对正确的规则。最后,政府的一位成员答应,在下一届会期里提出一项简短的法案,规定一下巴彻斯特和其他类似机构的管理办法。
下一届会期到来了。与习惯相反,那项法案也提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时正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一场大战可能爆发的最初迹象笼罩着全国[28]。海拉姆继承人的问题不论在议会内外,似乎都没有使很多人感觉兴趣。然而,那项法案一读、再读,并没有什么非难或异议,以一种不受人注意的方式通过了它的十一个程序[29]。约翰·海拉姆就这件事会怎么说呢?他能预料到,大约有四十五位先生会自行承担起责任来制定一项法律,改变他遗嘱的全部涵义吗?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希望内政部副大臣知道,因为这问题是得交给他去处理的。
可是,这项法案却通过了。大约在这部历史初开始的时候,法令规定,巴彻斯特养老院应当和先前一样,收容十二个老头儿,每人每天应得一先令四便士,另外还应当收容十二个老婆子,安顿在一所即将兴建的宿舍里,每人每天应得一先令二便士。此外,还应委派一名女舍监,年俸七十镑,有一所住宅;一名总管,年俸一百五十镑。后来又规定设置一名院长,年俸四百五十镑,他应当负责这两个机构的精神指导工作,以及男子养老院世俗事务的指导工作。主教、教长和养老院院长像从前那样,将轮流指派这个慈善机关内的受施人,职员一律由主教委派。法令中一句没有提院长应由大教堂圣诗班领唱人担任,也只字未提哈定先生对这一位置的权利。
然而,在老主教去世后好几个月,继任人刚就职不久,一份通告立即张贴出来,说明改革即将付诸实行。新颁布的这项法律和这位新主教的任命,全是一届新内阁——或者不如说是一届暂时让位给了对手、随即重又执政的内阁最早处理的工作。而格伦雷博士[30]的去世,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恰恰发生在政府更迭时期。
可怜的爱莉娜·波尔德!那寡妇的头巾披在她身上多么相称啊,还有她致力于自己新责任的那份严肃认真的神情。可怜的爱莉娜!
可怜的爱莉娜!我可不能说我曾经喜欢过约翰·波尔德。我始终就不认为他配得上自己娶到的这位妻子。不过在她看来,他却很配得上。她具有一颗那种依恋着自己丈夫的温柔的心,这倒不是出于偶像崇拜,因为崇拜是不能允许偶像有任何缺点的,而是带有常春藤的那种绝对的韧性。如同寄生植物甚至会仿效它攀附的那个树干的缺点那样,爱莉娜对丈夫的过失也依恋和爱护。她有一次曾经说过,不论父亲做了什么事,那些事在她看来总是对的。后来,她更换了效忠的对象,变得随时随地都准备为她的“老爷”最大的短处辩护了。
约翰·波尔德是一个惹女人怜爱的男子。他为人相当多情,又胸怀坦荡,很有丈夫气概。至于他妄自尊大,又没有出众的才干来作为后盾,以及他试图显得比邻居们高明,那么挫伤了熟人们的情感,这些全并不损害他妻子对他的崇拜。
就算她能够承认他有过失,他的未尽天年也会把这一点从她的记忆中抹掉的。她伤心哭泣,就像是失去了世上女子曾经获得过的一件稀世之宝那样。在他去世后好几星期,她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今后过得幸福的念头是可恨的。安慰,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难以容忍的,而泪水与睡眠便成了她仅有的解脱。
但是,树小不招风[31]。她知道自己腹中还有一个活生生的、需要她多方照顾的苗子。她知道,像上帝大发慈悲,会赐给她的那样,将要为她创造出另一个不知是祸是福的对象,另一个不知会给她带来莫名的欢乐还是令人绝望的悲伤的对象。起初,这只增添了她的悲伤!做一个可怜的婴孩的母亲,这有什么令人高兴的呢?这个婴孩还没有出世就成为孤儿,诞生在一个凄凉落寞的家庭的悲哀气氛里,在泪水与恸哭中给抚养大,然后没有父亲帮助照料便给送到世上去漂泊!这件事起初并没有给人什么欢乐。
然而,渐渐地,她的心情变得对另一样东西感到关怀了。在他出生以前,她带着一位渴望的母亲的热切心情期待着这个陌生人。恰恰在父亲下世以后八个月,另一个约翰·波尔德出世了。假如崇拜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不犯下什么罪恶的话,那么我们希望,献给这个没有父亲的婴儿的爱慕,可以不把它叫作一种罪恶。
我们在这儿来说明一下这孩子的性格,或者指出父亲身上的缺点在那个小小的胸膛中,有多少已经靠了母亲的德行而弥补掉了,这将是不值得的。这个孩子作为一个婴儿,是最最讨人喜欢的。我无法预见到我们有必要去调查一下他往后生活的事实。我们眼下在巴彻斯特的工作,至多不会占去我们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另一个人——倘有必要的话,——由他去写出小约翰·波尔德的传记吧。
不过作为一个婴儿,这孩子是十全十美的。谁也不想来否认这一事实。“他不逗人疼吗?”爱莉娜总对自己的父亲说,一面跪在那儿仰起脸来望着她父亲,亮晶晶的眼睛里满含着濡湿的泪水,年轻的脸蛋儿被寡妇的头巾紧裹着,两手抓住她宝贝儿子酣睡在里面的摇篮的两边。外祖父总欣然地承认,这个宝贝儿是很逗人疼,会吏长那位姨父也会表示同意,而爱莉娜的姐姐格伦雷太太便会带着姐妹之情十分爽快地来应和这句话。玛丽·波尔德——不过玛丽·波尔德是同一座神殿上的第二位礼拜者。
这个婴儿的确很逗人疼。他很起劲地吃着自己的食物,遇到两腿没给遮盖起来时,总欢快地把大脚趾支了出去,并且的确会突然发笑。这些据认为都是最健全的婴儿最大的长处,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咱们的婴儿全胜过了别的孩子。
这么一来,这位寡妇的悲痛心情便渐渐缓和了。她本来以为除了一死之外,没有别的能够医治好那个创伤,这时候一种芬芳的香油却给倒进了那个伤口。上帝待我们要比我们自己仁慈多少倍啊!在失去了每一张亲热的脸儿,在每一个心爱的人最后离去时,我们全认定自己将永远伤心,预期在流不尽的泪水中将自行消逝。这种悲痛多么难得能持久啊!上帝不容它这样,多么该享福啊!“让我永远记住活着的朋友,等他们死去以后便忘却他们,”这是一个深深领悟上帝的仁慈的聪明人的祈祷。也许,没有几个人会有勇气表示出这样一个愿望。然而这么做,只是求得那种从悲伤中的解脱,这一点是一位仁慈的造物主几乎总会给予我们的。
不过我可不希望人家以为,波尔德太太已经把丈夫全忘了。她带着夫妻恩爱之情天天想到他,把对他的怀念深深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深处。然而,她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却感到了快乐。把这个活生生的小人儿紧紧搂在怀里,感到有一个有生命的人,他现在的一切和往后的一切全都亏了她,他每天的食物都是她给的,他的那少量需要都是由她来满足的,他的小小的心眼儿首先就会爱上她,也只会爱上她,而他的稚嫩的舌头会第一次尽力用一个女人所能听到的最悦耳的名称来叫唤她,这一切多么美妙啊!因此,爱莉娜胸中慢慢平静下去,她热切而感激地肩负起自己的新责任来。
至于生计,约翰·波尔德撇下的寡妇家境很宽裕。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全留下给她,这包括一笔远远超出她和她的朋友们认为她需要的收入。它的数目每年将近一千镑。当她想到有这么大一笔钱时,她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使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后交给她丈夫的儿子,交给她自己的宝贝儿,交给这会儿正躺在她膝上酣睡的这个小男人。这个小人儿很幸福,对于为了他而不断增多的这种种操劳全一无所知。
约翰·波尔德去世以后,她恳切地请求父亲来和她同住,可是哈定先生谢绝了,虽然他曾作为来访的亲属,在她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他任人家怎么说,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一个家,因此继续住在巴彻斯特大街上一个药剂师铺子的楼上、他最初选中的那个小寓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