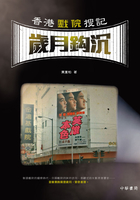
靚聲解畫員
香港電影資料館於1995年舉辦「香港早期電影軌跡(1896-1950)」展覽,當中「早期放映電影情況」部分,提及「早期電影皆為默片,放映商為求助興,會增設留聲機播放音樂,甚至僱用樂隊,現場伴奏;其後又有『解畫員』之設,專門講解劇情」,而「解畫員」在日本和台灣,往往成為「觀眾偶像,戲院生招牌,大名會刊在廣告旁,或張貼在影院門前。香港也有這個情形。」[10]
查看1926至30年期間的報章,戲院廣告雖有標示「每場均有解畫員」一類字眼,卻未見以偶像解畫員作招徠。雖然中西默片均有插入字幕,但英文並非人人皆懂,即使中國片提供中文字幕,但文盲為數仍不少,故戲院安排解畫員臨場解說。1926年7月,新世界戲院徵求解畫員,羅列五大資格:
(一)能了解西文字幕者;
(二)能以粵東方言譯述者;
(三)發音柔和,聲清而實,雅俗共賞,不帶土談及語病者;
(四)有世界常識者;
(五)平日對於電影有心得者。
該院期望徵得合適的解畫員,並提高解說水準,因為過往不少解畫員「隨隨便便,只求能夠把劇情解得出,便算盡其能事罷了」,另外又強調:「解畫員只須講字幕說明,但凡畫中人動作,或畫中景物,人人共見共識的,解畫員不須多費唇舌,免致節外生枝,反令觀眾討厭。」[11]
這段文字指出當時部分解畫員未盡其職,既有敷衍解說,更有說得過多。1927年,有觀眾撰文,規勸戲院別求濫竽充數,必須慎選解畫員。文中指陳各種毛病,例如常映古裝片戲院的解畫員,「對於劇情文字中之稍許深奧者,每大誤而特誤;而迎合齷齪心理之語,又每畫蛇添足以出之,且講至此等猥瑣之語時,目光灼灼,恆向後座瞻顧,意蓋以此為其解盡快心事然,故識者非之。」[12]
上文「向後座瞻顧」一語,似乎解畫員坐於某組觀眾席前,究竟他們坐於哪兒?2000年,《大公報》報導油麻地戲院的保育動向時,指出該院「開業初期,本港電影尚未普及,當時仍以上演粵劇為主,另外亦有放映一些默片,所以院方特在放映室內安放一排八呎高的長椅,作為解畫人的座位,而這排座位一直保留至八十年代初戲院大裝修時始被拆去。」[13]
這則報導的資料來源不詳,查看油麻地戲院開業首數年的廣告,稱為「影戲院」,映了不少默片,卻從未以演粵劇為主,反而後段寫放映廳置有供解畫員安坐的長椅,倒耐人尋味,說明解畫員坐於近後座位置;後座票價高,能較清晰的聆聽解說,亦屬合理。假如全院只有一位解畫員,那麼前方座位的觀眾便只能接收微弱的解說聲音,或許如此,有觀眾索性離座,走近解畫員細聽。
1930年10月下旬,灣仔的香港戲院放映《火燒紅蓮寺》夜場時,「因有解畫員演講影片事蹟,觀眾趨近聽講,致將院內交通甬道擁塞」。事件被副警司巡查時發現,該院便因映廳的通道被人群阻塞而遭政府檢控管理不善。[14]
沒機會親臨現場,不曉得解畫員如何為戲文發聲,相信不會平鋪直敍,依書直講,少不免裝腔作勢,增添趣味。粵語片年代的影人,如導演李化、吳回及演員黃侃,均曾在廣州的模範戲院當解畫員,[15]他們編導演的根源,大概當時已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