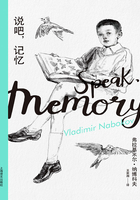
第三章
一
一位没有经验的纹章学家很像一个中世纪的旅行家,他从东方带回的,是在他一直拥有的本国动物的知识的影响下形成的对该地区特有动物的想象,而不是直接进行动物学探究的结果。因此在本章的第一个文本中,当我描绘纳博科夫家族的纹章时(多年前在一些家庭琐物中不经意地看过一眼),不知怎的竟把它扭曲成两只摆着姿势、中间放着一个大棋盘的熊的炉边奇景。现在我查找了那个纹章,失望地发现它其实是两只狮子——微带棕色,也许是有着浓密粗毛的野兽,但是并不真正是熊——正跃立着扬起前爪,侧身后顾、怒目而视,傲慢地展示着那不幸的骑士的盾牌,盾牌只不过是西洋跳棋盘的十六分之一那么大,青红两色相间,每一个长方格中有一个臂端有三叶花的银白色十字架。在它上方可以看见一个骑士的剩余部分:他坚硬的头盔和不能充当食物的护喉甲胄,以及从青红色叶状装饰中伸出来的一条勇敢的胳膊,仍在挥舞着一柄短剑。铭文是Za hrabrost’——“为了勇气”。
我在一九三〇年请教了父亲的表兄弟,热爱俄罗斯文物的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戈卢布佐夫,据他说,我们家族的奠基人是纳博克·穆尔扎(全盛时期一八三〇年左右),一位摩斯科维的俄罗斯化了的鞑靼亲王。我自己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博科夫是个博学的系谱学家,他告诉我,十五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莫斯科公国拥有土地。他让我参考一份关于一四九四年伊凡三世 时代发生在乡绅库里亚金和他的邻居卢卡·纳博科夫的儿子们菲拉特、叶夫多基姆和弗拉斯之间的农村争执的文件(收入一八九九年尤什科夫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三至十七世纪的法案》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纳博科夫家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和军人。我的高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一七四九—一八〇七)在保罗一世
时代发生在乡绅库里亚金和他的邻居卢卡·纳博科夫的儿子们菲拉特、叶夫多基姆和弗拉斯之间的农村争执的文件(收入一八九九年尤什科夫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三至十七世纪的法案》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纳博科夫家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和军人。我的高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一七四九—一八〇七)在保罗一世 统治时期是诺夫哥罗德卫戍团的团长,在官方文件中这个团被称做“纳博科夫团”。他最小的儿子,我的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博科夫在一八一七年的时候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那时他和未来的海军上将冯·兰吉尔男爵及李特克伯爵一起,在海军上校(后来成了海军中将)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的领导下,参加了绘制新地岛(竟然偏偏是这个地方)地图的考察,那儿的“纳博科夫河”是以我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在相当一部分地名中留下了对考察团领队的纪念,其中之一是西阿拉斯加的苏厄德半岛的戈洛夫宁环礁湖,霍兰博士描述过那里的一种名为Parnassius phoebus golovinus(应该加上个大大的“原文如此”)的蝴蝶;但是我的曾祖父除了那条非常蓝,几乎是靛蓝色,甚至是愤愤不平的靛蓝色的,在湿漉漉的岩石间曲折流淌的小河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可言;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了海军,n'ayant pas le pied marin
统治时期是诺夫哥罗德卫戍团的团长,在官方文件中这个团被称做“纳博科夫团”。他最小的儿子,我的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博科夫在一八一七年的时候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那时他和未来的海军上将冯·兰吉尔男爵及李特克伯爵一起,在海军上校(后来成了海军中将)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的领导下,参加了绘制新地岛(竟然偏偏是这个地方)地图的考察,那儿的“纳博科夫河”是以我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在相当一部分地名中留下了对考察团领队的纪念,其中之一是西阿拉斯加的苏厄德半岛的戈洛夫宁环礁湖,霍兰博士描述过那里的一种名为Parnassius phoebus golovinus(应该加上个大大的“原文如此”)的蝴蝶;但是我的曾祖父除了那条非常蓝,几乎是靛蓝色,甚至是愤愤不平的靛蓝色的,在湿漉漉的岩石间曲折流淌的小河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可言;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了海军,n'ayant pas le pied marin (告诉我关于他的情况的我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这样说的),调到了莫斯科近卫团。他娶了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纳济莫夫(十二月党人纳济莫夫的姐妹)为妻。我对他的军事生涯一无所知,不管他干的是什么,都无法和他哥哥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博科夫(一七八七—一八五二)相比,他是抗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之一,老年时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里面的一个囚犯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等作品的作者,宽厚的将军把书借给他看。然而有意思得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普希钦,普希金的同学和亲密朋友伊万·普希钦的姐妹。印刷者们,注意了:两个是“钦”,一个是“金”。
(告诉我关于他的情况的我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这样说的),调到了莫斯科近卫团。他娶了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纳济莫夫(十二月党人纳济莫夫的姐妹)为妻。我对他的军事生涯一无所知,不管他干的是什么,都无法和他哥哥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博科夫(一七八七—一八五二)相比,他是抗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之一,老年时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里面的一个囚犯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等作品的作者,宽厚的将军把书借给他看。然而有意思得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普希钦,普希金的同学和亲密朋友伊万·普希钦的姐妹。印刷者们,注意了:两个是“钦”,一个是“金”。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是伊万的侄子,尼古拉的儿子。他在两位沙皇手下当了八年的司法部长。他娶了在俄国部队服役的德国将军费迪南德·尼古劳斯·维克托·冯·科尔夫男爵(一八〇五—一八六九)十七岁的女儿玛丽亚为妻(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坚韧的古老家族中,某些面部特征不断反复出现,成了标志和缔造者的印记。纳博科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祖父的)是俄罗斯式的,软而圆的鼻尖向上翘起,侧面看去鼻梁稍稍往里斜;科尔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的)是一个帅气的德国式器官,有着醒目的鼻梁和稍稍昂起、鼻沟清晰的肉乎乎的鼻尖。高傲或感到惊奇的纳博科夫们扬起仅仅在中心部分有毛、因而眉梢往太阳穴方向越来越淡的眉毛;科尔夫家的眉毛弧度更优雅,但同样是相当稀疏的。除此之外,随着他们在岁月的画廊中变成一片朦胧,纳博科夫们很快就加入到了模糊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之中,对于后者,我只认识我的母亲和她的弟弟瓦西里,样本太少,对我眼前的目的没有什么用。而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到科尔夫家系的女子,都是花容月貌的美丽姑娘,她们有高高的红彤彤的颧骨、浅蓝色的眼睛,以及一边脸颊上那颗小小的痣,像贴上的美人斑,我的祖母、父亲、他的三四个兄弟姐妹、我二十五个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中的一些人、我的妹妹和我儿子德米特里都遗传到了,颜色深浅程度不同,但是多多少少仍然是同样印记的明显翻版。
我的德国曾外祖父费迪南德·冯·科尔夫男爵于一八〇五年出生在柯尼斯堡,他娶了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希什科夫(一八一九—一八九五),度过了很有成就的军人生涯后,于一八六九年在萨拉托夫附近他妻子的沃尔甘领地上去世。他是冯·科尔夫男爵威廉·卡尔(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和冯·德·奥斯滕–萨克恩女男爵埃莱奥诺尔·玛加丽塔(一七三一—一七八六)的孙子,普鲁士部队的少校尼古劳斯·冯·科尔夫(一八一二年去世)和安托瓦妮特·泰奥多拉·格劳恩(一八五九年去世)的儿子。安托瓦妮特·泰奥多拉·格劳恩是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 的孙女。
的孙女。
安托瓦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一七六〇年生)娘家姓菲舍尔,是出生在哈通家的雷金娜(一七三二—一八〇五)的女儿,雷金娜是柯尼斯堡一家著名出版社社长约翰娜·海因里希·哈通(一六九九—一七六五)的女儿。伊丽莎白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女。她在一七九五年和第一任丈夫、那位作曲家的儿子Justizrat 格劳恩离婚后,和一个不甚著名的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冯·斯特奇曼结了婚,而且是一个有名得多的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一七七七—一八一一)的——按告诉我的德国人的说法——“慈母般的朋友”。克莱斯特三十三岁的时候热恋上了她十二岁的女儿黑德维希·玛丽(后来是冯·奥尔菲斯)。据说他在出发到万湖——和一个病弱的女士一起去执行自杀的约定——去之前到她家去告别,但是没有被准许进门,因为那天是斯特奇曼家洗衣服的日子。我的祖先和文学家之间的接触在数目和多样化上确实十分惊人。
格劳恩离婚后,和一个不甚著名的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冯·斯特奇曼结了婚,而且是一个有名得多的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一七七七—一八一一)的——按告诉我的德国人的说法——“慈母般的朋友”。克莱斯特三十三岁的时候热恋上了她十二岁的女儿黑德维希·玛丽(后来是冯·奥尔菲斯)。据说他在出发到万湖——和一个病弱的女士一起去执行自杀的约定——去之前到她家去告别,但是没有被准许进门,因为那天是斯特奇曼家洗衣服的日子。我的祖先和文学家之间的接触在数目和多样化上确实十分惊人。
我的曾外祖父费迪南德·冯·科尔夫的曾外祖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于一七〇一年 出生在萨克森的瓦伦布吕克。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格劳恩(一六七〇年生)是个税务官(“Königlicher Polnischer und Kurfürstlicher Sächsischer Akziseneinnehmer”
出生在萨克森的瓦伦布吕克。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格劳恩(一六七〇年生)是个税务官(“Königlicher Polnischer und Kurfürstlicher Sächsischer Akziseneinnehmer” ——所论及的选帝侯,即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是他的同名人),来自牧师世家。他的高祖父沃尔夫冈·格劳恩一五七五年时是普劳恩(离瓦伦布吕克不远)的风琴手,如今,他的后代、那位作曲家的雕像装点着那儿的一座公园。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于一七五九年五十八岁时在柏林去世,十七年后,那里的新歌剧院以他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作为开张的首场演出。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根据被他的皇室保护人
——所论及的选帝侯,即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是他的同名人),来自牧师世家。他的高祖父沃尔夫冈·格劳恩一五七五年时是普劳恩(离瓦伦布吕克不远)的风琴手,如今,他的后代、那位作曲家的雕像装点着那儿的一座公园。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于一七五九年五十八岁时在柏林去世,十七年后,那里的新歌剧院以他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作为开张的首场演出。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根据被他的皇室保护人 的悲伤所感动的当地的讣告撰写人所写,甚至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门采尔
的悲伤所感动的当地的讣告撰写人所写,甚至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门采尔 所作的腓特烈大帝
所作的腓特烈大帝 用长笛吹奏格劳恩的作品的画幅上(格劳恩已经去世),格劳恩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多少有点超然地站在那里;在我流亡的年代里,这幅画的复制品始终跟随着我走遍我待过的每一个德国公寓。据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有一幅当代的绘画,表现的是格劳恩和他的妻子多萝西娅·雷克普坐在同一架拨弦古钢琴前。音乐百科全书常常翻印柏林歌剧院里他的那幅画像,在画像中他看上去很像我的堂兄弟、作曲家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从往昔的流金岁月传回了一个有趣的小小的回声:在彩绘的穹顶下所有的那些音乐会的收入之中,二百五十美元之多的一笔钱于一九三六年在“嗨,希特勒”的柏林平淡地到达了我的手里。那时格劳恩家庭的限嗣继承的财产,主要是一批漂亮的鼻烟盒和其他珍贵的小摆设,在经历了普鲁士国家银行的许多变化之后,已经缩减到四万三千德国马克
用长笛吹奏格劳恩的作品的画幅上(格劳恩已经去世),格劳恩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多少有点超然地站在那里;在我流亡的年代里,这幅画的复制品始终跟随着我走遍我待过的每一个德国公寓。据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有一幅当代的绘画,表现的是格劳恩和他的妻子多萝西娅·雷克普坐在同一架拨弦古钢琴前。音乐百科全书常常翻印柏林歌剧院里他的那幅画像,在画像中他看上去很像我的堂兄弟、作曲家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从往昔的流金岁月传回了一个有趣的小小的回声:在彩绘的穹顶下所有的那些音乐会的收入之中,二百五十美元之多的一笔钱于一九三六年在“嗨,希特勒”的柏林平淡地到达了我的手里。那时格劳恩家庭的限嗣继承的财产,主要是一批漂亮的鼻烟盒和其他珍贵的小摆设,在经历了普鲁士国家银行的许多变化之后,已经缩减到四万三千德国马克 (约一万美元),钱被分给了这位有远谋的作曲家的后代:冯·科尔夫、冯·维斯曼和纳博科夫家族的人(第四个家族,即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伯爵家族,已经灭绝了)。
(约一万美元),钱被分给了这位有远谋的作曲家的后代:冯·科尔夫、冯·维斯曼和纳博科夫家族的人(第四个家族,即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伯爵家族,已经灭绝了)。
两位冯·科尔夫男爵夫人在巴黎警察部门的刑事档案中留下了她们的痕迹。一个是一位瑞典银行家的女儿,做姑娘时名字叫安娜–克里斯蒂娜·施特格尔曼,是俄军上校弗罗姆霍尔德·克里斯蒂安·冯·科尔夫男爵的遗孀,他是我祖母的曾叔祖父。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是另一个军人、著名的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的表妹或心上人或两者都是;正是她,一七九一年在巴黎把自己的护照和定做的簇新的旅行用四轮马车(一个有着高大的红色车轮的豪华东西,座位的靠垫都是乌得勒支 丝绒做的,有深绿色的窗帘和各种当时很时髦的精巧装置,如vase de voyage
丝绒做的,有深绿色的窗帘和各种当时很时髦的精巧装置,如vase de voyage )借给皇室供他们出逃到瓦雷讷
)借给皇室供他们出逃到瓦雷讷 ,皇后假冒是她,国王假冒两个小孩的家庭教师。另外一个与警察有关的故事牵涉到的伪装不具有这么大的戏剧性。
,皇后假冒是她,国王假冒两个小孩的家庭教师。另外一个与警察有关的故事牵涉到的伪装不具有这么大的戏剧性。
一个多世纪前在巴黎,随着狂欢节周的来临,莫尔尼伯爵邀请了“une noble dame que la Russie a prêtée cet hiver à la France” (如亨利斯在一八五九年《画刊》第二百五十一页的“宫廷报道”部分中所报道的)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化装舞会。这位贵妇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尼娜,冯·科尔夫男爵夫人;她五个女儿中的老大玛丽亚(一八四二—一九二六)就要在同年,即一八五九年的九月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结婚,他是科尔夫家的朋友,当时也在巴黎。为了这次舞会,男爵夫人为玛丽亚和奥尔加各定制了一套花童女装,每件二百二十法郎。根据那位笔底生花的《画刊》的记者的报道,这笔费用等于六百四十三天“de nourriture,de loyer et d'entretien du père Crépin)[食物、房租和鞋子]”的开销所需,听起来很怪。服装做好了以后,科尔夫夫人觉得“trop décolletés”
(如亨利斯在一八五九年《画刊》第二百五十一页的“宫廷报道”部分中所报道的)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化装舞会。这位贵妇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尼娜,冯·科尔夫男爵夫人;她五个女儿中的老大玛丽亚(一八四二—一九二六)就要在同年,即一八五九年的九月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结婚,他是科尔夫家的朋友,当时也在巴黎。为了这次舞会,男爵夫人为玛丽亚和奥尔加各定制了一套花童女装,每件二百二十法郎。根据那位笔底生花的《画刊》的记者的报道,这笔费用等于六百四十三天“de nourriture,de loyer et d'entretien du père Crépin)[食物、房租和鞋子]”的开销所需,听起来很怪。服装做好了以后,科尔夫夫人觉得“trop décolletés” ,拒绝接受。女裁缝叫来了huissier(法警),他们争吵得很厉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丽,急躁易怒,而且,我遗憾地说,个人道德方面远不如从她对待低领口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么严格)起诉女裁缝要求损害赔偿。
,拒绝接受。女裁缝叫来了huissier(法警),他们争吵得很厉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丽,急躁易怒,而且,我遗憾地说,个人道德方面远不如从她对待低领口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么严格)起诉女裁缝要求损害赔偿。
她声称店里送服装来的女孩子是些“des péronnelles[粗鲁无礼]”的女子,在她提出衣服领子开得太低,不适合有教养的淑女穿的时候,作为回答,她们“se sont permis d'exposer des théories égalitaires du plus mauvais goût[竟敢极端低级趣味地炫耀民主思想]”;她说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定制别的化装舞服,她的女儿们没有去参加舞会;她指控法警和他的随行懒散地倒在软椅上,却让女士们坐硬椅子;她还火冒三丈,愤怒地抱怨说,法警竟然还威胁说要把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先生,“Conseiller d'État,homme sage et plein de mesure[一个庄重、沉默寡言的人]”,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这位绅士试图把法警从窗子里扔出去。这算不上什么大官司,但是女裁缝输了。她收回了衣服,退了钱,外加给原告一千法郎;另一方面,做马车的人在一七九一年交给克里斯蒂娜的约五千九百四十四里弗赫 的账单,这笔钱根本就没有偿付过。
的账单,这笔钱根本就没有偿付过。
从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五年一直任司法部长的德米特里·纳博科夫,顶着反动势力的猛烈攻击,尽他所能地就算没有加强至少也保护了六十年代自由派的改革(例如陪审团审判)。一位传记作家说:“他的表现很像风暴中一艘船的船长,会把部分货物抛到海里去,以保全其余的货物。”(布罗克豪斯 百科全书俄文本第二版)我注意到,这个悼文式的比喻无意中回应了一个铭文式的主题——我的祖父此前要把法律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企图。
百科全书俄文本第二版)我注意到,这个悼文式的比喻无意中回应了一个铭文式的主题——我的祖父此前要把法律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企图。
在他退休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让他在伯爵的头衔和一笔钱——想来是笔大数目——之间进行选择。我不知道伯爵的爵位在俄国究竟价值几何,但是和节俭的沙皇所希望的相反,我祖父(他的伯父伊万在尼古拉一世 让他做出类似的选择时,也是这样决定的)坚决选择了更为实在的奖赏。(“Encore un comte raté。”
让他做出类似的选择时,也是这样决定的)坚决选择了更为实在的奖赏。(“Encore un comte raté。”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冷冰冰地评论道。)退休后他多数时间住在国外。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他脑子开始糊涂了,但是他坚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区,一切就不会有问题。医生们的看法相反,认为在某个山中胜地或在俄国北方的气候下他可能会活得长一些。有一个关于他在意大利某处摆脱了随从的惊人故事,我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拼串起来。他在那里四处乱转,以李尔王式的愤怒,向咧着嘴笑的陌生人痛斥他的子女,直到在一片多石的荒野地带被一个缺乏想象力的carabinieri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冷冰冰地评论道。)退休后他多数时间住在国外。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他脑子开始糊涂了,但是他坚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区,一切就不会有问题。医生们的看法相反,认为在某个山中胜地或在俄国北方的气候下他可能会活得长一些。有一个关于他在意大利某处摆脱了随从的惊人故事,我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拼串起来。他在那里四处乱转,以李尔王式的愤怒,向咧着嘴笑的陌生人痛斥他的子女,直到在一片多石的荒野地带被一个缺乏想象力的carabinieri 抓住。一九〇三年冬天在尼斯,我的母亲始终在他的身边,她是老人神经错乱的时刻唯一能够容忍在他左右的人。我和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和我们的英国女家庭教师一起,也在那儿。我记得窗玻璃在欢快的轻风中格格作响,以及一滴热火漆滴在我的手指上引起的令人惊奇的疼痛。我一直在用蜡烛的火焰(我跪在石板地上,入侵的阳光使火焰变淡,成了骗人的苍白色)把熔化的火漆棒变成大红的、蓝的和古铜色的气味特别好闻的黏糊糊的小团。不一会儿我躺在地板上惨叫起来,母亲赶来搭救,坐在轮椅里的爷爷在附近某处用拐杖使劲敲打发出回声的石板地。她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艰难。他说粗话。他老是把沿英国人漫步街推他散步的护理人员误认做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内阁的一个(早已去世)的同事。“Qui est cette femme—chassez-la!”
抓住。一九〇三年冬天在尼斯,我的母亲始终在他的身边,她是老人神经错乱的时刻唯一能够容忍在他左右的人。我和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和我们的英国女家庭教师一起,也在那儿。我记得窗玻璃在欢快的轻风中格格作响,以及一滴热火漆滴在我的手指上引起的令人惊奇的疼痛。我一直在用蜡烛的火焰(我跪在石板地上,入侵的阳光使火焰变淡,成了骗人的苍白色)把熔化的火漆棒变成大红的、蓝的和古铜色的气味特别好闻的黏糊糊的小团。不一会儿我躺在地板上惨叫起来,母亲赶来搭救,坐在轮椅里的爷爷在附近某处用拐杖使劲敲打发出回声的石板地。她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艰难。他说粗话。他老是把沿英国人漫步街推他散步的护理人员误认做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内阁的一个(早已去世)的同事。“Qui est cette femme—chassez-la!” 当比利时或荷兰王后停下来问候他的健康的时候,他会用颤巍巍的手指指着她们对我母亲这样大声喊道。我依稀记得跑到他的椅子前给他看一块漂亮的鹅卵石,他慢慢地仔细看着,然后慢慢放进了嘴里。我真希望在母亲后来回忆这些岁月的时候,我有更强烈的好奇心。
当比利时或荷兰王后停下来问候他的健康的时候,他会用颤巍巍的手指指着她们对我母亲这样大声喊道。我依稀记得跑到他的椅子前给他看一块漂亮的鹅卵石,他慢慢地仔细看着,然后慢慢放进了嘴里。我真希望在母亲后来回忆这些岁月的时候,我有更强烈的好奇心。
他会越来越长久地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其中有一次他被转移到了在圣彼得堡皇宫码头他的住所里。随着他意识的逐渐恢复,母亲把他的卧室伪装成他在尼斯的卧室的样子。找到了几件类似的家具,让人专门把一些物件从尼斯急送过来,还弄来了所有他模糊的意识习惯了的花,种类和繁盛都恰到好处。从窗子里能够望得见的屋子的一小片外墙被刷成亮白色,这样,当他每次回复到比较清醒的状态时,就会发现自己安全地处在我母亲精巧策划出的幻觉中的里维埃拉 。就在那里,在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平静地去世了,一天也不差地整整比我父亲早十八年。
。就在那里,在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平静地去世了,一天也不差地整整比我父亲早十八年。
他身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长子是德米特里,他继承了在当时沙皇的波兰领土上的纳博科夫长子继承地产;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莉迪亚·爱德华多芙娜·法尔茨–费恩,第二个是玛丽·雷德利希;次子是谢尔盖,米滔的总督,他娶了达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图奇科夫,她是斯摩棱斯克公爵、陆军元帅库图佐夫 的玄孙女;下一个是我的父亲。最小的儿子是康斯坦丁,一个坚定的单身汉。女儿们是:纳塔丽娅,俄国驻海牙领事伊万·德·彼得森之妻;薇拉,运动员和土地所有者伊万·皮哈切夫的妻子;尼娜,和华沙军事总督劳施·冯·特劳本堡男爵离婚后,嫁给了日俄战争中的英雄、海军上将尼古拉·科洛梅茨耶夫;伊丽莎白嫁给了亨利,赛恩–维特根斯泰因–贝尔勒堡大公,他去世后又嫁给了她儿子们过去的家庭教师罗曼·利克曼;娜杰日达,德米特里·冯里亚利亚尔斯基的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
的玄孙女;下一个是我的父亲。最小的儿子是康斯坦丁,一个坚定的单身汉。女儿们是:纳塔丽娅,俄国驻海牙领事伊万·德·彼得森之妻;薇拉,运动员和土地所有者伊万·皮哈切夫的妻子;尼娜,和华沙军事总督劳施·冯·特劳本堡男爵离婚后,嫁给了日俄战争中的英雄、海军上将尼古拉·科洛梅茨耶夫;伊丽莎白嫁给了亨利,赛恩–维特根斯泰因–贝尔勒堡大公,他去世后又嫁给了她儿子们过去的家庭教师罗曼·利克曼;娜杰日达,德米特里·冯里亚利亚尔斯基的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
康斯坦丁叔叔在外交界服务,在他事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在伦敦和萨布林就二者之中谁来领导俄国使馆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失败的斗争。他的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起伏变故,但是他两次绝妙地逃脱了比在一九二七年要了他的命的伦敦一家医院的穿堂风要凶险一些的命运。一次是在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谢尔盖大公在爆炸前半分钟提出让他搭自己的马车走,我叔叔说谢谢,不用了,他想步行。于是马车驶向了和恐怖分子的炸弹的致命约会。第二次是在七年以后,他又一次失约了,这回是和一个冰山,是由于碰巧退掉了泰坦尼克的船票。我们逃出了俄国后在伦敦和他有很多来往。一九一九年我们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见面在我脑子里是一个生动的插曲:我父亲大步走到他拘谨的弟弟面前紧紧地拥抱他,而他后退着连连说:“Mï v Anglii,Mï v Anglii[我们是在英国]。”他可爱的小公寓里满是来自印度的纪念品,如年轻的英国军官的照片等。他是《外交官的考验》(一九二一年)一书的作者,在大型公共图书馆里很容易找到这本书,他还出版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 的英文本。他连同山羊胡子等等一起出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门大厅左侧的一幅朴次茅斯和约
的英文本。他连同山羊胡子等等一起出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门大厅左侧的一幅朴次茅斯和约 签字场面的壁画上(和威特公爵、两个日本代表以及和善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我和一个鳞翅昆虫学家同事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姓氏用金色的斯拉夫字符书写在那儿,觉得是个特别恰当的地方——对我认出来时发出的惊呼,他的应答是:“没错,没错。”
签字场面的壁画上(和威特公爵、两个日本代表以及和善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我和一个鳞翅昆虫学家同事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姓氏用金色的斯拉夫字符书写在那儿,觉得是个特别恰当的地方——对我认出来时发出的惊呼,他的应答是:“没错,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