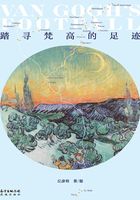
辑一 踏寻梵高的足迹
津德尔特(Zundert)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进行巴黎城市彻底改造工程计划,开启巴黎时髦优雅的风采。在西方: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英国建成水晶宫,是为现代建筑的先驱工程之一;法国科学家傅科用摆的实验证明了地球自转;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成功,旋即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十年,次年底自封拿破仑三世,登基称帝。在东方:中国正是清朝文宗皇帝在位的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领导的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下南京建都;清廷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清军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从此引发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与清朝敌对的“太平天国”岁月。但这也是中国积极输入各种西学第二期的肇始。

津德尔特梵高中心

◇ 津德尔特梵高故居纪念碑(左)和津德尔特政府大楼(右)
中国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乱,没有引起一般西方人的关注,他们在意的是法国的政变,拿破仑王朝的复苏。何况,他们正沉浸在科学实验发展和现代建筑创造新奇的喜悦中。
一八五三年,文森特·梵高出生在荷兰津德尔特小镇的一个牧师家庭里,是荷兰新教牧师西奥多勒斯·梵高和妻子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斯的长子。
谁都不会料到,这个婴儿,远在二十世纪后能在人类艺术史上造成轰动与重要影响,成为知名度最大、最普遍的艺术家。如今,他留下的画作,价格是天价。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建有梵高美术馆,是观光客必游的胜地之一。他生前的书信、他的画册、有关他的传记和研究论文,各种文字比比皆是。

◇ 津德尔特梵高故居(下),以及提示梵高故居的海报(上左)、门牌号(上右)
一九九〇年后,我便长居荷兰,但直至二〇〇五年八月五日,唐效才开车带我,圆了拜访梵高出生地津德尔特镇的心愿。
其实从住家到津德尔特镇并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只要是周末假期,随时都可到这个小镇转一圈。我却在住到荷兰十五年之后,方才来到这里。也许正因为太容易来到,没有了紧迫感,便有所谓无所谓地拖延着了。
说来也是巧合。我去家庭医生迪克特斯处看病。一如往常,握完手,进入正题说病情前,这位帅气、幽默的家庭医生,总会和我闲话,聊几句家常,说个冷笑话。这次讲到绘画,提及梵高。
“知道梵高在哪里出生?”迪克特斯医生问。
这么简单的问题,哪能考得倒我?我立即脱口回答:“津德尔特。”
他赞许地点头:“你知道津德尔特出了几位名人?”紧接着考我。
这下,我可傻了。除了梵高,还真不知津德尔特出过什么其他名人。
我的家庭医生这下得意了,微笑着宣布谜底:“梵高和你的家庭医生。”
“什么?你生在津德尔特?”我有些惊奇,有点怀疑他在开玩笑。
他正经点头道:“是的,我是津德尔特人。虽不是出生在梵高家那幢房子里,但在同一条街上,离得很近。”
津德尔特的“两位名人”,一位照顾我的身体健康,一位影响我的精神生活。两位都与我的生活关系密切,这才有了走访津德尔特的积极行动。探访中不仅多了一份感情,也增加了趣味。
津德尔特镇正如其他荷兰小镇,清清幽幽。来到地方政府大楼前的红砖广场,区政府的白色大建筑物,方正庄严地矗立,隔着广场、一条大马路与一排衔接的砖房相对。政府大楼正前方的屋宇——呈山形屋顶装饰的一幢褐赭色砖房,竖立着一根高耸的旗杆,旗帜在空中展开。大幅的旗帜印刷着梵高戴草帽自画像,写着“这儿曾是文森特·梵高家的房子”。细看大门旁边,砖墙上镶了一块水泥板,雕饰着一只鸟站立于柔软的草叶上,记录: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梵高诞生于此。
荷兰各城镇到处可见的一幢普通坚实的砖房,因为水泥板上的几个字,这幢房屋立刻显得意义非凡。
梵高去世前,居住在法国小城奥维,从他租赁的房间窗户望出去,也是隔条马路面对着广场,广场后即市政厅。
生与死的环境,居然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巧合?!当梵高在奥维的小房间凭窗凝望,举起画笔画下该地市政厅的画幅时,是否曾回忆起童年的家,而泛起温馨的微笑?
从梵高出生房子前面的马路,往上直走不过百来米,与他家同一侧有一个小广场,被命名为“梵高广场”。广场中央搭建起一个略为高起的平台,上面放置一座细长的雕像:两个身穿西装外套的男子相拥而立,脸贴着脸,手执着手,足并着足。这个直截了当表现兄弟之情的当代雕塑,是津德尔特镇为纪念文森特·梵高与西奥·梵高 ,交由艺术家奥西普·扎德金(Ossip Zadkin)所制成的作品。从雕塑侧面望向后方,背景的深绿树荫下,是一座在暗影中浮现的宁静肃穆的小教堂。
,交由艺术家奥西普·扎德金(Ossip Zadkin)所制成的作品。从雕塑侧面望向后方,背景的深绿树荫下,是一座在暗影中浮现的宁静肃穆的小教堂。

◇ 梵高父亲任职的教堂(左)和津德尔特的木制风车(右)
教堂外低矮的围栏上了锁,无法进入教堂巡礼,我便沿着围篱绕看,已具年代、孤独直立的小教堂外表砖墙、四周高擎而枝叶浓密的大树与墓园,追怀梵高。
当年梵高父亲在此侍奉上帝,这里也是幼年梵高除了家教之外,接受宗教熏陶最重要的场所。梵高的悲天悯人与宗教情怀,就是在这儿孕育出来的了。
开着车,唐效与我把津德尔特镇的大街小巷全部游逛一番,连偏远一点的木造风车 ,也去观览了一番,一张巨大、木质有些朽坏的早年风车叶片,静置在修复好的风车旁边,供人凭吊臆想。
,也去观览了一番,一张巨大、木质有些朽坏的早年风车叶片,静置在修复好的风车旁边,供人凭吊臆想。
不像近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城市乡镇大兴土木,大多较久远的历史印痕都被毫不吝惜地抹去,小镇虽因年代变迁,盖了许多新建筑,但由于荷兰人对于人文历史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仍能在夹杂的古老屋宇与存留的砖石街道中,轻而易举地捡拾起过往的岁月。梵高兄弟以及他们的玩伴,曾在这些地方穿梭玩耍的情景,在相隔一百多年之后,我还能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何其幸运。
一八六〇年,梵高进入出生地津德尔特的乡村小学就读,全校约两百个学生,仅有一名教师。梵高父母对此小学的教育不满意,他们发现儿子和农家的男孩子混在一块儿,言行举止受到影响变得粗鄙。因此一八六一年开始,梵高和妹妹安娜不再上学,父母特别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专门教导两个学龄期的小孩,直至一八六四年九月。
在儿童时代的故乡,一八六二年,九岁的梵高画出了最早的素描,他用铅笔画桥、搅牛奶的桶还有狗。一八六三年,画了蓟菊、柱头、一小束花。纯粹是小孩子涂鸦,何况梵高也没有表现出对画图的特别热情,谁会料到这孩子长大之后,几经生活的历练、工作跑道的转换,竟会走上从事作画的艺术工作,而且戏剧性地在他去世后,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传颂至今。
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九年,梵高先赴泽芬贝亨镇,再到提耳堡市住读,但每逢假期则返回津德尔特家中。假期,他与妹妹安娜帮扬·多门做园艺,也帮扬·凡·阿特森放羊,赶着山羊沿树篱、小径到处游荡。他常常被家中的女仆米安巧·洪考普惩罚,在她眼中梵高总是不安分,行为古怪。
梵高童年即对阅读怀有强烈的热情,学习了多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和德语。这段时日,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开始了西式教育,有了英文的教学。在津德尔特,在父母注重教育的培养下,小梵高平顺地度过了童年与少年。
虽然只用很短的时间走了一遭津德尔特,却因多年居住荷兰,了解荷兰人的文化习俗,我已经从朴实宁静的小镇感受到了梵高的成长。
津德尔特,一个属于荷兰北布拉邦省的小乡镇。我长年居住的考克区也隶属同一省份,我早已深深领会北布拉邦省人性情的温暖,小地方人与人互助的亲密,以及对于宗教的虔敬。
梵高在法国圣雷米疗养期间,画了不少追想北布拉邦省的图画,金光灿美、风景宜人,他的心情我懂。
一八六九年,十六岁的少年梵高,离开出生地津德尔特之后,再没回来过。但津德尔特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他曾写道:“哦!津德尔特,有时回想起来,非常清晰强烈。”也叙述道:“我在画布上努力创作,正如津德尔特人,在他们的农田里辛勤工作。”故乡大自然的美丽,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太阳在树林后方转变成红色,沼泽地上反射着黄昏的气味,荒野与黄色、白色、灰色的砂土,充满了色调和气氛。这种生活中短暂少许的一瞥,让我们的心中获得平静。我们的生命似乎朝这样的荒野走去,但并非经常如此。
津德尔特之行,虽没能探看梵高曾经礼拜过的小教堂内部,心中并不觉太遗憾。
猜想自己亦如梵高的离去,不会再次刻意前来津德尔特抚今追昔,但小镇的景象却将常驻心底。